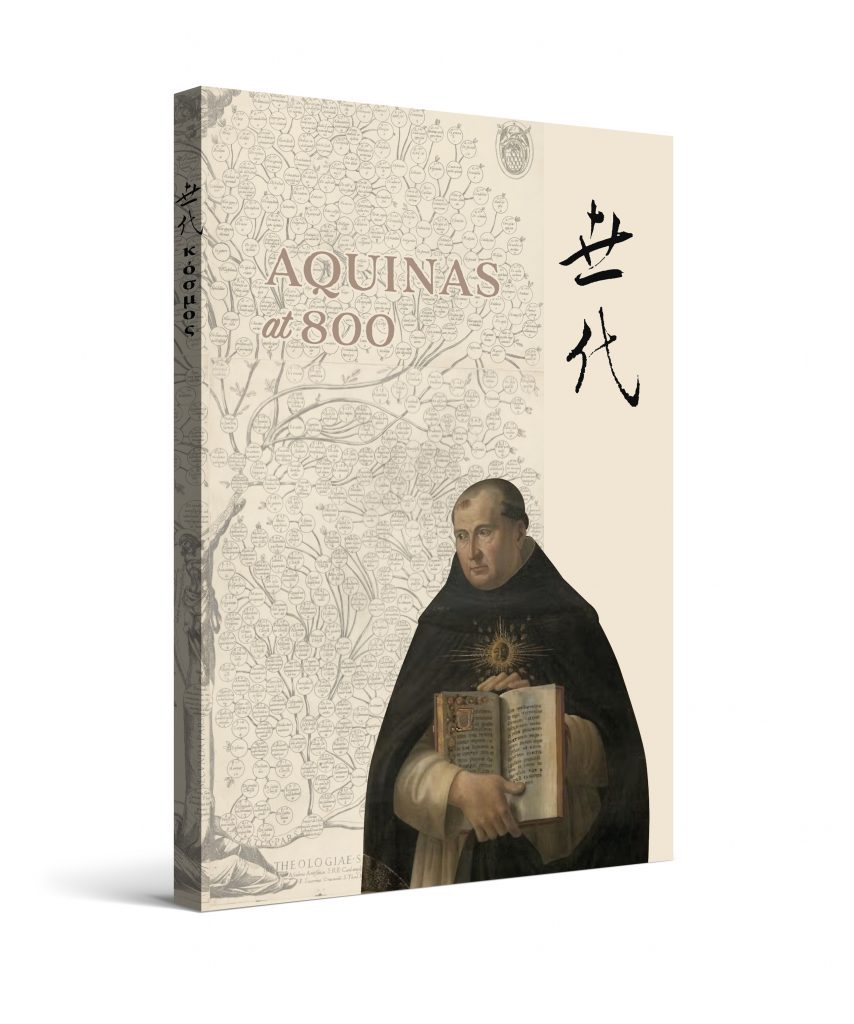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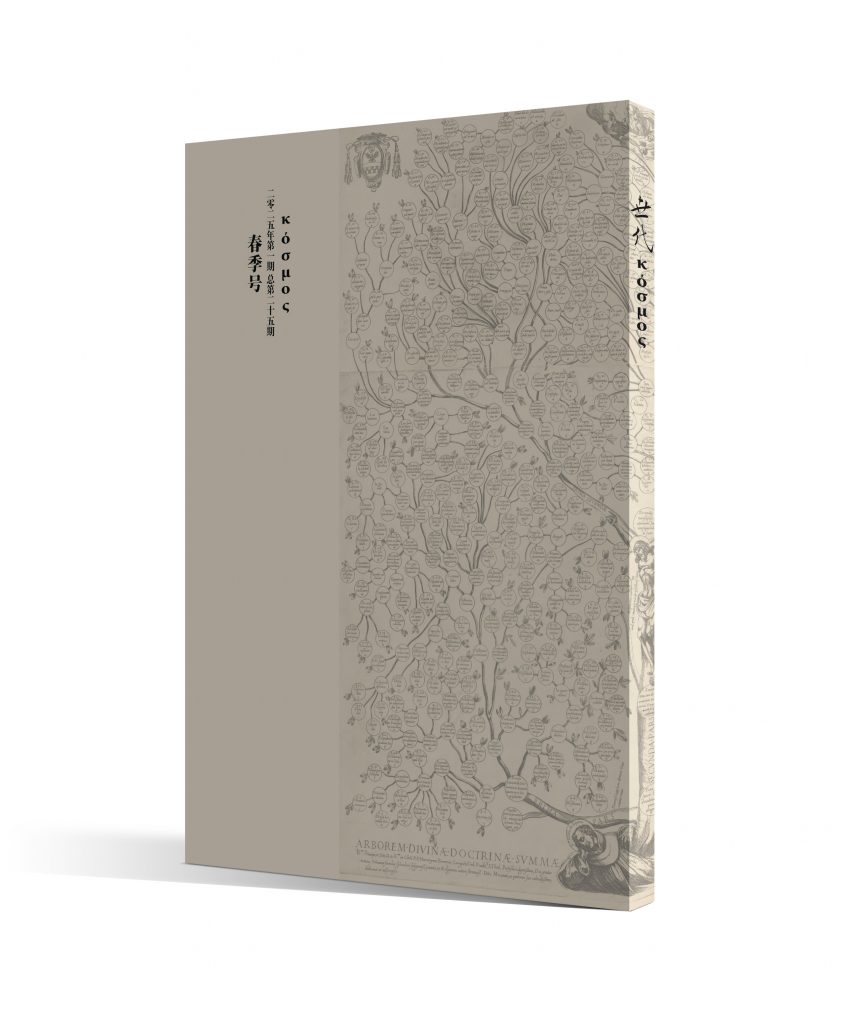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出生年份,尽管有1226年乃至1227年之说,不过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仍是1224年或1225年。<1> 据此,人们或以去年或以今年为阿奎那诞辰800周年。去年一年,中外学界均召开了规模不等、主题各异的纪念会议。<2> 而在今年,由台湾中华道明会和碧岳学社联合出版的阿奎那《神学大全》中译本(2008年出版),其简体字版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在内地付梓发行,以此献礼大公教会史上这位神学巨人800周年诞辰纪念。作为一份关注历史与思想的基督教刊物,本刊今春联合北京橡树文字工作室推出“纪念托马斯·阿奎那诞辰800周年专刊”,可谓恭逢其盛。
或许有人会质疑,阿奎那既然是天主教神学家,与基督教新教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新教也要参与是次纪念呢?确实,阿奎那去世近半个世纪就被教宗若望二十二世(John XXII)封圣(1323年),1567年又被时任教宗庇护五世(Pius V)宣布为“教会博士”(Doctor of the Church),所著《神学大全》更是在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期间享受与圣经和教宗教令并列的殊荣。1879年,阿奎那的神学思想被确立为对天主教教义的权威性阐释。<3> 在通常的观念中,宗教改革既然反对的是罗马天主教,自然就要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官方代表阿奎那,而宗教改革的儿女——今天的基督新教,即便不反对阿奎那,至少也要与这位天主教神学家保持距离,更不用说纪念他的诞辰了。
要驳斥这种偏见,只需指出阿奎那生活在宗教改革之前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阿奎那的思想遗产属于大公教会的传统,不能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与新教分庭抗礼,天主教对阿奎那思想的一系列“垄断”,新教就不得不将大公教会的这一宝藏拱手相让。既然阿奎那属于整个大公教会,那么承接早期教会使徒性和大公性的基督新教,自然可以从托马斯的神学中受益。
不过,更为严肃的反对意见则认为,改教家中的两座高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当初不是反对阿奎那的神学吗?持此论者举出1517年秋,也就是在维滕堡教堂贴出举世闻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前几个月,路德张贴《驳经院神学论纲》97条,站在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立场,指控经院神学(包括托马斯主义)已经向帕拉纠主义缴械投降。<4> 在路德看来,建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院神学所主张的救恩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以行为称义。因此,为了向世人显明何为真正的基督教神学,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神学必须走下神坛。<5>
然而,仔细阅读这份《论纲》,就会发现路德所反对的经院神学,主要指的是他此前曾受教的经院神学中以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 1287—1347)和比尔(Gabriel Biel,约1420—1495)为代表的新路派(via moderna,又称作唯名论),这种神学传统据说偏离了中世纪经院神学盛期为安瑟伦(Anselm,1033—1109)和阿奎那所秉承的奥古斯丁救赎论传统。前者在称义问题上主张神人合作,人们可凭自己努力行善、拒绝罪恶来蒙受上帝的恩典和接纳,其实是帕拉纠思想的翻版。<6> 学者们怀疑路德是否真正直接阅读过托马斯的著作。比尔在一些神学议题上固然准确阐释了托马斯的主张,但在关于罪、恩典和称义等方面则误读了托马斯。特别是在自然与恩典这个议题上,比尔留给路德的印象是,托马斯是一个半帕拉纠主义者。这其实是对托马斯的误解,相反,在诸如预定论、救赎和恩典等教义方面,托马斯是一个奥古斯丁主义者。<7>
换言之,路德是透过新路派的滤镜接触阿奎那的神学。他与经院神学的决裂,与其说是与阿奎那的决裂,不如说是与他的奥卡姆师辈们分道扬镳。说路德反对阿奎那,实在是一种相当简单化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8>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路德对托马斯神学态度消极,但这并不代表新教阵营的全部。与路德同时代的改教家,比如马丁·布塞(Martin Bucer,1491—1551)、维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1499—1562)、赞奇(Jerome Zanchi,1516—1590)、梅兰西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等人,其实都是托马斯主义者。<9>
加尔文反对阿奎那这一说法的根据,可能来自《基督教要义》中的几处说明,不过也有学者质疑该反对的真实性。<10> 事实上,与路德类似,加尔文所谴责的不具名的经院神学家,未必专门针对诸如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大师,而是指当时一些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秉承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教师。“看似是对经院哲学的全盘谴责,实则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并非如此,而是有着具体的针对对象。加尔文或许会为了驳斥某个具体的对象,而谴责一整个门类的思想。”如果对比加尔文和阿奎那两人的预定论,会发现二者虽有侧重,但极为接近,因为二人都接近奥古斯丁而反对帕拉纠。<11>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基督教要义》早期版本(比如1559年版)的行文结构,明显受到经院哲学辩论模式的影响。加尔文表面上对经院哲学家的负面评价,并不能代表他对中世纪经院神学及其方法、主题和特点的全部看法,拒绝的同时也有借用,有时则是直接引用。<12>
总之,与过去学术界强调改教家中的司各脱主义和奥卡姆主义成分不同,当今大多数学者认为托马斯主义是早期改教家哲学和神学思考中的重要因素,当然其中不乏取舍。尽管学界仍有争论,但对于早期的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而言,托马斯主义至少是他们遵循的一项重要的思想传统。<13> 甚至有学者研究《神学大全》后得出结论说,虽然大多数改教家及其跟随者对阿奎那和《神学大全》评价负面,但是16世纪后期兴起的所谓“新教经院主义”(Protestant scholasticism)则呈现出另一种复杂面相,即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特别是阿奎那的神学有选择的借鉴。<14>
不但如此,对17世纪新教学校的研究也表明,当时人们热衷于使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和援引经院哲学家来捍卫新教教义,并与当时罗马天主教内部兴起的经院哲学新趋势展开对话。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就智识方面而言,18世纪中期的后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特别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之间不是断裂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连续性。<15>
这种广泛存在于改教家与阿奎那思想之间的连续性,相信在阅读本期文章的过程中,读者将不难发现。不仅如此,读者还会发现,阿奎那基于基督信仰的幸福论对于今人思想何为幸福的人生仍有丰富的启示意义。并且,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阿奎那首先不是一位中世纪哲学大师,而是一位跟随基督的门徒、大公教会卓越的圣师。我们今天纪念他,就像纪念历世历代被上帝特别使用的圣徒那样,当然与圣徒崇拜没有关系,而是因为相信这个时代的我们,仍然需要重拾这位神学巨擘留给大公教会的丰厚遗产。
<1> Jean-Pierre Torrell, OP.,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ume 1, The Person and His Work, third edition, translated by Matthew K. Minerd and Robert Royal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23), 2.
<2>国内外相关的纪念会议,比如2024年6月8—9日,于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中世纪哲学论坛——纪念阿奎那诞辰8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世纪哲学专业委员会2024年会”。据报道,与会人员有来自包括港台地区近3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70余人。见《中国社会科学网》网站,2024年6月12日。https://www.cssn.cn/zx/zx_rdkx/202406/t20240612_5758230.shtml 。国外方面的纪念规模更为隆重,比如去年9月22日到25日,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580余名与会者(其中包括近200名圣母大学学生和当地不少社区人士)齐集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召开纪念托马斯诞辰800周年大会。据称该会三天半的议程中有超过150名讲员,论题包括幸福论、圣经神学、存在现实(the actus essendi)、公民身份、教会合一、先知知识、基督论、三一神学、法理论、灵魂论、道德论、形而上学、生物增强(bioenhancement)、商业等方面。无论就规模还是议题范围而言,后者远超前者。见美国圣母大学雅克·马里坦研究中心(Jacques Maritain Center)网站https://maritain.nd.edu/news/maritain-center-hosts-historic-aquinas-at-800-conference/
<3>参阅Paul van Geest, Harm Goris, Carlo Leget eds. Aquinas as Authority: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Thomas Instituut te Utrecht, December 14-16, 2000 (Leuven Peeters, 2002), introduction, VII.
<4>“驳经院神学论纲”(1517年),见伍渭文主编,《路德文集》第一卷(改革运动文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2025年第二次印刷,第55—63页。另参考“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 in Luther: Early Theological Works, edited by James Atkins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266-273。
<5>“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 introduction, in Luther: Early Theological Works, edited by James Atkinson, 263.
<6>参见“驳经院神学论纲”第6、10、55、91条。Matthew Barrett, The Reformation as Renewal: Retrieving the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Academic, 2023), 169-172, 281-283. 有关新路派或者唯名论思想主张的简介,参阅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1—72页。
<7> Matthew Barrett, The Reformation as Renewal: Retrieving the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167-168.
<8>参阅Karl-Heinz zur Mühlen, “On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in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in Paul van Geest, Harm Goris, Carlo Leget eds. Aquinas as Authority, 65-86.
<9>“Luther Among the Anti-Thomists,” in David C. Steinmetz, Luther in Con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48,58.
<10>如《要义》3.2.8:“我们必须反驳经院神学家们对形成和未形成之信心所做的毫无价值的区分。”脚注列有阿奎那《神学大全》出处。再比如《要义》3.14.11:“事实上,他们将重生之人的义描述为:人一旦借着信心信靠基督与神和好之后,就在神面前以善行的功德被算为义。”脚注亦列《神学大全》出处。见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册,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2017年重印,第538、774页。另见英译本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ume 1, edited by John T. McNeill, translated and index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551,778.Raith指出McNeill-Battles的《要义》英译本在许多地方误引阿奎那,给读者造成加尔文批评阿奎那的印象。事实上,加尔文攻击的神学与阿奎那的神学并不是一回事。《要义》中译本延续了英译本的误植。见Charles Raith II, Aquinas and Calvin on Romans: God’s Justification and Our Particip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
<11> David C. Steinmetz, “The Scholastic Calvin,” in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Essays in Reassessment, edited by Carl R. Trueman and R. Scott Clark (Eugene, Oregon: Wipf& Stock Publishers, 2005), 26-27, 30. Steinmetz在这篇文章中总结道,加尔文与经院哲学的关系比我们原以为的复杂得多。他对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有轻视亦有尊重,有借用、模仿又有误解。他的神学和释经双重进路与经院哲学相似,特别是他赋予教会以学校功能的神学思考,显明了经院神学理念的民主化及扩展。
<12>比如Muller就认为,1559年版的《要义》标注出的行文结构,仿照了经院哲学的辩论模式:提出陈述——各种反对——回应反对。后续的版本,包括目前流行的McNeill-Battles译本,则以评论注释的方式淡化了这一结构。见Richard A. Muller,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46, 57.
<13> Aquinas Among the Protestants, edited by Manfred Svensson and David VanDrunen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8), 11-12.
<14> Bernard McGinn, Thomas Aquinas’s Summa theologiae: A Biograph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1.
<15> Jordan J. Ballor, “De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Thomas Aquinas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in Aquinas Among the Protestants, edited by Manfred Svensson and David VanDrunen, 43.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5期的主题是“纪念托马斯·阿奎那诞辰800周年”,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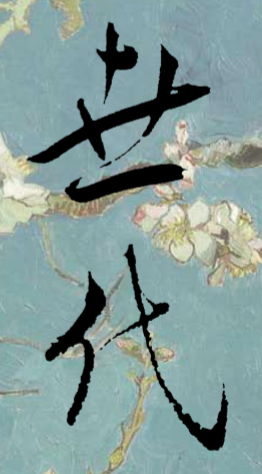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