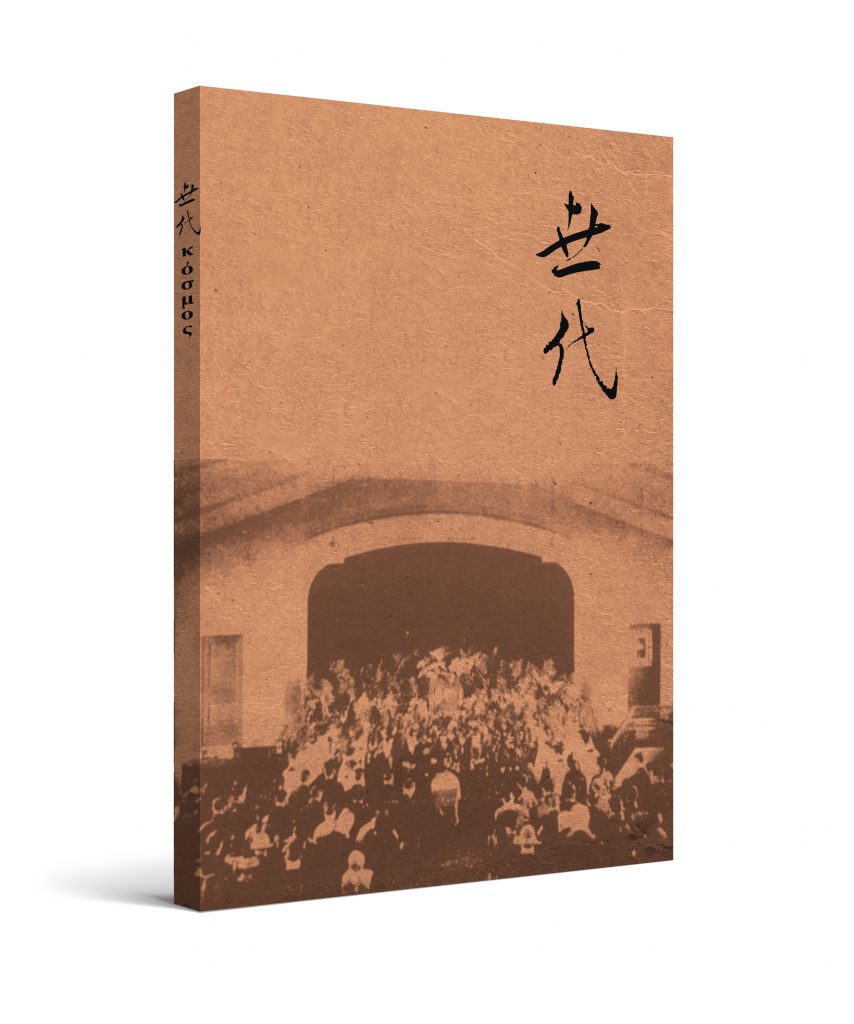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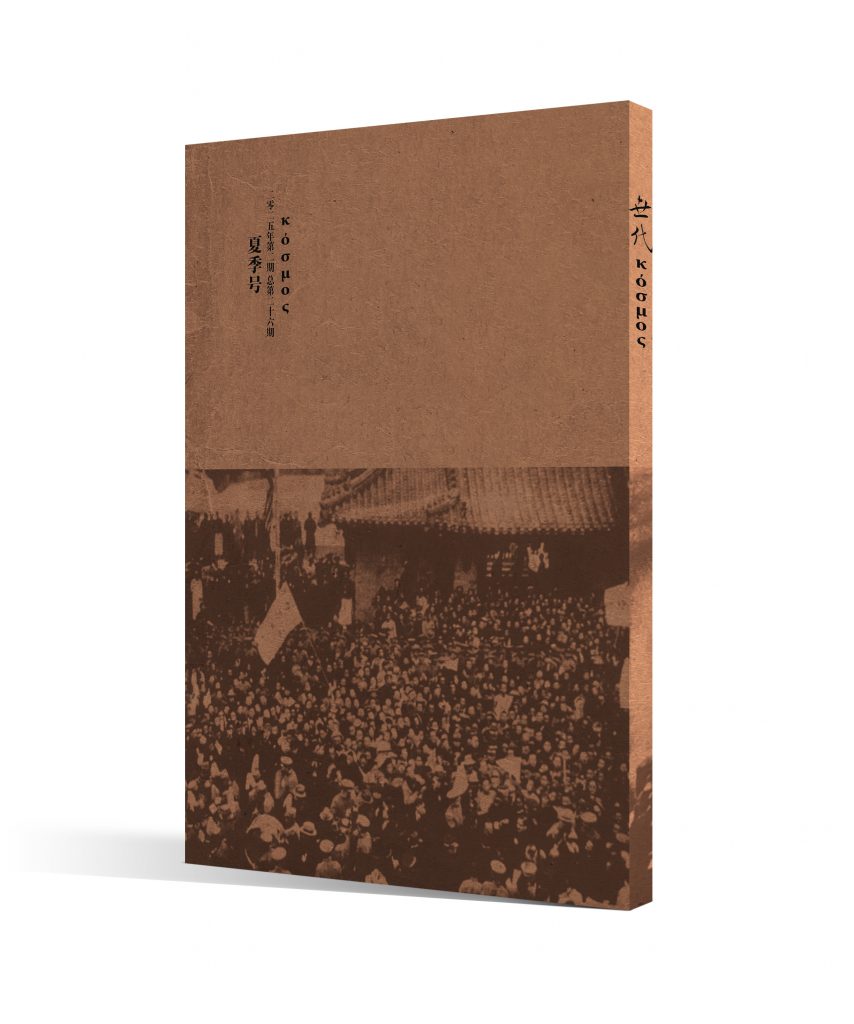
据说,孙中山(1866—1925)生前曾回答日本友人,读书是其三大爱好之一。<1> 他身旁的随侍人员也证明其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无论境遇顺逆几乎手不释卷,无日不读。阅读是孙中山吸取新知、陶冶性情并形成革命学说的主要方式。<2> 他不但自己读书,也劝人读书。1918年7月26日,在给其子孙科(1891—1973)的信中,孙中山就劝其珍惜时间读书治学,还对孙科送来的《宗教破产》一书非常欣赏,赞其“殊为可观”。除此之外,他对怀特的《基督教领域里的科学与神学之争》、柏格森的《生元有知论》二书也有好评。<3>
这封信所开列的三本书,提供了探究孙中山信仰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一条线索,表明他熟悉当时西方世界关于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争论,特别是了解“基督教进化论者”这一群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基督教与进化论、宗教与科学并非截然对立,至少在现代神学领域中,存在调和的一派。<4> 明乎此,当五年后孙中山在广州欢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说,就人类来源于上帝六日创造还是由动物进化而来,表示“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5>,就不宜如以往某些研究那样,遽然得出孙中山晚年批判基督教、倾心唯物论甚至是无神论者这样的结论。<6>
之所以对孙中山的宗教观出现这样的误判,主要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者对基督教的认识有限<7>,对材料的解读与分析粗疏<8>,往往仅就孙中山的片言只语分析其宗教观念,易陷论者所说的“自由心证”<9>,即选取符合自己立场的材料来行文,导致要么淡化要么夸大基督教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其代价是掩盖了孙中山思想的复杂性。
以上仅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例,简要揭示以往研究孙中山的宗教观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近年来有关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重心似乎逐步由孙中山的生前转向死后<10>,探讨孙中山的基督教葬礼、中外教会人士对孙中山历史记忆和基督徒形象的构建<11>,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缺少对孙中山宗教观特别是对其基督信仰状况的切实把握,有关孙中山身后与基督教相关的研究和评价,难免因缺少某个可供衡量的恰切参照点而略显不足。<12> 当然,要做到对孙中山基督信仰的切实把握并不容易,一方面因孙本人未留下对基督教专门系统的文字表述,而且众所周知,他对基督教有过从起初的热心到后来淡漠的变化,另一方面既是挑战也是可能的一个探讨方向是,将孙中山独特的基督教信念置于20世纪以来的现代神学思想光谱中来观察,并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将其宗教神学与其他同时代的基督徒精英人物比较,以呈现其独特之处。
100年前,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国民党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后来写道,虽然孙中山已经去世,但作为精神领袖,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任何时候。“一旦他溘然长逝,人们就可以把他变为完人”。<13> 与公开举行的追悼盛况相比,孙中山家人亲友为其举办的基督教追思礼拜(家祷礼)则鲜有人知。时人与今人一样,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希望孙中山留给公众的历史记忆,首先是革命领袖和“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主持孙中山追思礼拜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1891—1947),曾在纪念孙中山的悼文中说,“他(即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还要待百年之后,国民把后此的经验与成绩,和中山先生事业之结果与影响比较而观,方能亲切,方能作公允的结论”。<14> 其实相应也可以说,孙中山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位置,他与基督教的关系,百年之后的今天不失为检讨的难得契机。此为本刊夏季号以“孙中山与基督教”为主题的用意所在。
本期的主题文章有两篇。《基督徒形象的塑造——以孙中山追思礼拜为中心的考察》回顾百年前那场充满争议、至今很大程度上仍鲜为人知的基督教葬礼,主要考察了当时中国基督徒精英群体对孙中山基督徒形象的塑造,揭示其对外回应非基运动对内满足信仰认同的双重用意,指出其代价是无限放大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无视其政治人物的首要身份和另类的信仰观念。文章还概括了孙中山基督教信仰中四点争议之处,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感化中国:孙中山的思想征途》聚焦孙中山人生的后期,宗教与政党意识形态对其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对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影响。文章通过历史性考察孙中山对“感化”(意为改造或皈依)的概念化过程,其中涉及观念、体系与实践,来剖析其政治宗教性。作者认为,孙中山结合基督教与苏俄意识形态而提出并实践的“感化”,是20世纪革命宣传即将兴起的一个早期范例。
本期还收到了两篇专文。《阿奎那论作为首要神学德性的信心》,以《神学大全》文本为据,首先概述阿奎那的信心概念,再分别探讨了信心和救恩、真理、知识、信经、基督、三位一体等六方面的关系,以呈现阿奎那信心观丰富而深邃的神学内涵。《何为圣经接受史?》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何为圣经接受史。作者分梳接受史的概念资源——效果史与接受史,进而探究这一概念资源影响下的圣经接受史之性质问题,并尝试为圣经接受史下定义,指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多元主义的当代社会中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此外,本期还收录了孙毅老师阅读《薛华的人生智慧:逆主流文化的属灵生命》一书后的书评,在介绍基督教思想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经历的教会分裂和信仰危机之后,作者认为现代人同样需要建立起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世界观,来应对这个真相不明的时代施加给我们的挑战。方激的短篇小说《木桩》,则让我们看到历史车轮呼啸而过之下,小人物对承诺的信念与持守展现出来的可敬力量。
<1>《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陈鹏仁译,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30页。
<2>黄季陆,“国父的读书生活”,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5—840页。
<3>“致孙科函”(1918年7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1—482页。
<4>参见冯志弘,“进化论与基督宗教:孙中山的观点”,《清华学报》新46卷第1期,2016年,第121—160页。该作者考证孙中山《致孙科函》提到的《宗教破产》一书,并非编者所注尼采的《上帝之死》,实为Joseph McCabe, The Bankruptcy of Religion (London: Watts & Co., 1917)。
<5>“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20—321页。
<6>如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五集,1987年,第15、22页;张金超、李红伟,“孙中山与宗教关系管窥”,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https://bj.crntt.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10523&secid=10668
<7>比如上个世纪80—90年代初相关学者,主要依据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来看待基督教。除前引陈建明外,尚有张子荣,认为孙中山“未能从根本上识别宗教具有的麻痹作用,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故对帝国主义存有天真的幻想。”(“孙中山与基督教会”,《晋阳学刊》1987年第6期,第66页。)田海林总结道,在孙思想的后期,科学扳倒了神学。基督教也是一种精神鸦片。不但如此,“宗教是现实的一种反动”,影响了孙对列强本质的认识,削弱了革命家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田海林,“论孙中山宗教思想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2卷第4期,第35页;郑永福、田海林,“孙中山与基督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9卷第4期,第99页。)
<8>比如一些研究者就受到《孙中山全集》编者的误导,以为《致孙科函》提及的《宗教破产》即为尼采的《上帝之死》,未做深究,据此得出孙中山悖离基督教的结论。如朱宇,“论孙中山的宗教观”,《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5卷第4期,第122页;董丛林,“孙中山宗教观的近代政治、文化蕴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1卷第1期,第132页。需要注意的是,两文重复之处颇多。
<9>见苏远泰,“孙中山与基督教”,《建道学刊》1998年第9期,第104页。
<10>借用李恭忠语。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页。相关的研究综述,参考聂林林,“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研究:回顾与评论”,《近代中国》第23辑,2014年,第88—105页。
<11>如林辉锋,“孙中山基督教葬礼问题再探——从宋庆龄与斯诺的一段纠葛谈起”,《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刘家峰、王淼,“‘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杨卫华,“孙中山政治形象的建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比较”,《史林》2020年第3期。
<12>比如前引林辉锋的文章,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晚清民国基督徒比拟为第二代“两头蛇”,认为他们与明末清初的第一代“两头蛇”一样,面临中西文化冲突的困惑,而且还要经受宗教信仰与民族感情、革命理念的某种紧张。这种比附忽略了两个事实:以孙中山为例,晚清民国基督徒精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拘囿远不如明末清初的奉教人士那么深刻强烈,他们所感到的文化挣扎与紧张要小得多;其次,孙中山等革命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耶稣当做革命者,他们的基督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救国使命的,二者间所谓的“紧张”即便可能存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
<13>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尚营林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14>刘廷芳,“中华基督徒与孙中山”,《生命》1925年3月,第90页。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6期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基督教”,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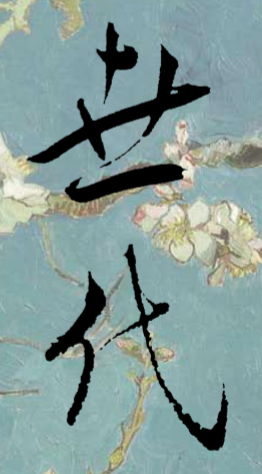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