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圣经》。荷兰画家赫里特·道(Gerrit Dou,1613—1675)作于约1645年。来源:维基百科]
内容摘要:近几十年来,圣经接受史成为圣经研究的热点议题。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对圣经接受史的理论反思也在进行中;圣经接受史的诠释学基础与性质、范围与任务,至今仍聚讼纷纭。本文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旨在重新探讨何为圣经接受史。第一部分分析接受史概念的前身,亦即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使用的效果史概念。第二部分梳理姚斯(Hans Robert Jauss)根据效果史概念所发展出的接受史概念。第三部分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影响下的圣经接受史,厘清它与圣经研究其他相关方法与学科的关系,并且重新探讨圣经接受史的性质问题。结论部分为圣经接受史下定义,初步勾勒出圣经接受史以及中国圣经接受史的研究框架,并提出圣经接受史研究在多元主义的当代社会中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圣经接受史、伽达默尔、效果史、姚斯、接受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Karl Marx)<1>
的确,有许多史学书写和史学研究的模式。毫无疑问,每一种史学观察都以对效果史的有意识反思为其基础。北美洲爱斯基摩人部落的历史,确实与这个部落是否、以及何时编入“欧洲的普遍历史”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不能真的否认,效果史的反思即便对于这一史学课题而言也是重要的。无论谁在半世纪、或一世纪后重新读我们今天所写成的这个部落的历史,他不仅会发现这个历史已经过时了——因为那时他将知道更多的东西、或者更正确地解释原始资料;而且他也会看到,在1960年,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这些原始资料的,因为他们是被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成见和不同的兴趣所支配。如果我们想让史学书写和史学研究完全避开效果史研究的领域,那么最终而言,史学书写和史学研究将会归于无有。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本身,先于对历史所产生的每一种兴趣,因为这种普遍性涉及到对“历史问题”而言总是根本性的东西。没有“历史问题”的史学研究算是什么呢?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2>
导论
近几十年来,“接受”(reception)、“效果”(effect)、“影响”(influence, impact)、“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 reception history)或“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 effective history, history of effects, history of influence, impact history)<3>等词汇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圣经研究之中。哥斯利(James G. Crossley)曾指出,圣经接受史的研究成为新约研究的热门议题。<4>就英语世界的出版物而言,其一,以“接受”为关键词的相关工具书(词典、手册或百科全书)至少有:《圣经及其接受简明词典》(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2009)<5>;《牛津圣经接受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e Bible,2013)<6>;最令人瞩目的是德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出版社德古意特(Walter de Gruyter)从2009年起出版的《圣经及其接受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EBR),该百科全书的出版目标是30大卷、预计总共有9000条目。<7>
其二,以圣经接受史为旨趣的丛书至少有:“布莱克维尔圣经注疏”(Blackwell Bible Commentaries, BBC),2004年出版第一本《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天启》(Revelation: The Apocalypse of Jesus Christ)<8>;“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教会圣经系列”(The Church’s Bible Series);以及同样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的“圣经及其接受研究”系列(Studies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2013年出版《迦南妇人的驯服:在马太福音15章21—28节中建构基督徒身分》(The Taming of the Canaanite Woman: Constructions of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Afterlife of Matthew 15:21–28)。<9>
其三,以“接受”为关键词的“学术期刊”,包括《宗教与接受研究》(Relegere: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Reception)、《圣经接受》(Biblical Reception)以及同样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的《圣经及其接受杂志》(Journal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随着接受史——或者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接受批判(reception criticism)以及接受释经(reception exegesis)——在圣经研究中的兴起,从理论上、尤其从哲学诠释学上对圣经接受史这一核心概念的反思也在进行中。圣经接受史的诠释学基础与性质、范围与任务,至今仍聚讼纷纭。因此,重新探讨圣经接受史这一概念,有助于厘清圣经接受史的基本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哲学反思与实践运用铺路。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何为圣经接受史?欲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何为接受史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可一分为二,一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哲学诠释学中使用的效果史概念(第一部分);二是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根据效果史概念所发展出的接受史概念(第二部分)。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进而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影响下的圣经接受史,厘清它与圣经研究其他相关方法与学科的关系,并且重新探讨圣经接受史的性质问题。结论部分为圣经接受史下定义,初步勾勒出圣经接受史以及中国圣经接受史的研究框架,并提出圣经接受史研究在多元主义的当代社会中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一、效果史
(一)效果史:(圣经)接受史的前身
圣经接受史一词由圣经和接受史两个词合成,因此在讨论何为圣经接受史之前,首先要处理何为接受史。就诠释学的发展而言,文学诠释学者姚斯首倡的接受史概念,又必须追溯到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曾指导过姚斯的老师、20世纪哲学诠释学的领军人物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效果史概念;在此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分析姚斯的接受史如何继受、又如何挪用伽达默尔的效果史。简单而言,效果史是接受史的诠释学前身,而接受史在继受效果史重要内涵的同时,既改变了侧重点(从更强调文本变成更强调读者),也改变了性质(从原则或意识变成方法或学科)。本节首先讨论效果史的概念。
伽达默尔在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一书的第二大部分(“真理问题扩大到人文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之“一种诠释学经验理论的基本特征”这一章中,阐述了效果史的概念。更具体地说,效果史主要在“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这一节中被予以阐述;在此,伽达默尔提出了“效果史原则”的问题。作为一种原则的效果史究竟是什么?伽达默尔为何在作为诠释学原则的“理解的历史性”这一节中提出效果史原则?效果史在哲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性又在哪里?
(二)效果与历史
效果史的德文Wirkungsgeschichte是一个合成词,分别由wirkungs(effects, influence, impact)与geschichte(history)这两个德文单词组成(这一点《真理与方法》似乎并未论述)。可以翻译成“效果”(或“效用”、“效应”、“结果”、“影响”等)的德文单词wirkungs,指的是某原因产生的某结果,或某事件、行动或人改变他人或他事的方式。而翻译成“历史”的德文单词geschichte,值得更进一步讨论。
按照马素尔(I. Howard Marshall,1934—2015)的考察——他的语境并非直接关涉效果史或哲学诠释学,而是关涉历史耶稣研究中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诠释学(也因此并非与哲学诠释学毫无关联)——英文中表达“历史”的名词只有history,但是德文中表达“历史”的名词却有两个,分别是historie与geschichte,并且分别对应两个形容词historisch(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historical)与geschichtlich(具历史重要性的,historic)。两个德文名词的分别在于,historie指的是任何一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historisch)事件(并不考虑该事件对后世重要与否),而geschichte指的是“具历史重要性的”(geschichtlich)事件,亦即“构成历史里重要的一环”的事件,或相比于其他历史事件而言更重要的事件。换言之,historie可以包罗万有,但是geschichte只包括少数事件。<10>这样看来,我们姑且可以将historie译作“曾发生过的历史”,而将geschichte翻译成“具历史重要性的历史”。<11>
德文中两种意义的“历史”之分,会产生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什么事情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实际上必须由诠释该事件的史学家作出判别和挑选。一个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并不知道其是否有后果、有多大后果,因此根本无从讨论它是否具有历史重要性;对某个事件是否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判断,总是需要事先考虑到该事件“后来的效果”或“无效果”。<12>
既然对某个事件之历史重要性的判断,总是依赖于作为诠释者或读者的史学家根据某种特定标准、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某个时间——事件与史学家之间的时间距离——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来进行(过去与后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诠释学循环);那么某个事件是否具有历史重要性、是否对后世发挥影响力,就至少不仅仅是由事件本身的意义来决定,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更大范围的历史、甚至是所谓的普遍历史以及置身于这一历史长河之中(而永远无法抽身其外)的诠释者或读者的——套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deger,1889—1976)的术语——前有、前见、前把握<13>所决定。
简言之,某个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并非以一种绝对客观、不变的方式存在,亦非不证自明。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诠释者或读者)与他的研究主题(即过去的历史或过去历史中的某事件)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关系;而对该事件的理解以及该事件所呈现的意义,也总是在对话中才不断产生出来。
(三)效果史与理解的历史性
在分析了德文中wirkungs(效果)一词的意思,以及geschichte(具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一词的内涵和背后隐藏的困难之后,我们要回过头来提问:由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Wirkungsgeschichte一词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究竟是何含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在这段话中他第一次引出效果史的概念:
所谓的历史主义,之所以说它幼稚,就在于它没有进行这种反思(引者按:即反思历史思考自身的前见),并且由于相信它自己的做法是根据一定的方法,因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性。这里,我们必须摆脱一种被糟糕理解的历史思考,转而诉诸于一种可以更好执行理解之任务的历史思考。真正的历史思考必须考虑到历史思考自身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历史思考才会停止追逐一个历史对象——不断进步之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学会将对象视为与历史思考自身处于同等地位的相对物,并因而理解对象与历史思考这两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我和他者的统一,或是一种关系——这一种关系同时由历史的实体与历史理解的实体所构成。一种恰当对待主题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之内显示历史的实体与历史的效果。我就把它称之为效果史(history of effect, Wirkungsgeschichte)。在本质上,理解是一个效果史事件。<14>
在这段引文中,伽达默尔尝试讨论何为一种更好的历史思考,即一种更恰当地描绘当我们说我们在理解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历史思考。“更好”就意味着比较。的确,伽达默尔在此借着批评以往那种糟糕的、历史主义式的历史思考,而倡导更好的、效果史式的历史思考。但是,所谓以历史主义为指导的历史思考问题出在何处?伽达默尔给出的答案是:19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影响下的历史主义因为没有反思自己的前见,而忘记了理解的历史性。Sinéad Murphy在研究效果史的专著中指出,浪漫主义以来的历史主义在历史思考上的幼稚在于,它假设了一个非历史性的研究者,这个研究者可以站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外,不会将研究者自身的任何东西(前见)带入研究中。<15>
但是,伽达默尔根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诠释学现象学指出,在我们作为诠释者试图理解之先,我们就已经存在于世界中(being-in-the-world)——“海德格尔的论点是:存在本身就是时间。”<16> 理解不再首先是一个方法论概念,而首先就是存在本身。我们存在,所以我们理解。同时,我们总是在时间中、亦即总是在历史中来理解;没有哪一刻的理解,可以超脱时间与历史。无法超脱时间与历史,也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带着某些东西进入理解之中;在理解之前,我们总是已经理解了某些东西(诠释学循环<17>)。这所谓的“某些东西”,伽达默尔称之为诠释者的前见。而我们不可能在本体论意义上摆脱前见,即意味着诠释者总是受到塑造这些前见的传统的影响(哪怕我们未必意识得到)。更重要的是,前见为诠释者提供了特定的视域(Horizont),借此诠释者才得以登高望远。<18>如此说来,理解的历史性本身就是诠释学理论的首要特征。诠释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完成了从认识论(理解是某种方法)到本体论(理解就是存在)的转向。<19>伽达默尔则完全继受了海德格尔的思考。
因此,从理解本质上是历史性这个角度来看,历史思考不再如历史主义那样地用不偏不倚、绝对中立的方法,不带任何前见地获取真理与知识。相反,如伽达默尔所言,历史思考必须考虑到历史思考自身的历史性。<20>换言之,所谓的历史对象绝非客观、独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关系,即历史现象与历史现象影响下(也就是历史现象的效果)、带有前见的历史主体这二者所构成的关系。如此,伽达默尔所定义的效果史,就是这样一种诠释学原则:它在理解本身之内并非只显示历史的实体,而是同时显示历史的实体与历史的效果。
伽达默尔说理解是一个事件、而且是一个效果史的事件,也就意味着在理解中,可以看到一个诠释学循环,这个循环是过去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传统文本)与后来的诠释者(读者)之间的对话、而非某一方的独白。一方面,因为时间距离的缘故,历史现象的视域与诠释者的视域绝非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因为诠释者的理解又必然受到传统的影响(历史是有效果的,且正是历史的效果才使诠释者的理解成为可能),所以二者又绝非完全不同。在历史现象与读者之间出现的“疏远的距离化”(alienating distanciation)与“归属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belonging)——根据利科(Paul Ricoeur)对《真理与方法》的评论<21>——二者的争论,恰恰使得效果史原则(既关注历史本身、又关注历史的效果)必不可少。
这也正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一节中探讨效果史原则的原因。作为(诠释学)原则的效果史,隶属于上升为诠释学原则的“理解的历史性”。因此,效果史原则是理解的历史性原则的逻辑延伸:“在本质上,理解是一个效果史事件。”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19世纪中期法国政局的分析中有一段生动论述,可以作为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和效果史原则的一个绝佳注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2>
二、从效果史到接受史
(一)作为原则或意识的效果史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出版之后,一再反对将自己主张的本体论诠释学与以往探讨方法的认识论诠释学混为一谈。一方面,就整体的哲学诠释学而言,伽达默尔表示,自己的目的并非如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等人的传统诠释学那样撰写一份指南来指导人们如何进行理解:“我并不希望阐述一系列的规则来描述——更不用说来指导——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程序。”<23> 在一封写给意大利法律史家Emilio Betti的信中,伽达默尔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学说绝非提出方法(他反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帝国主义),而是描述了实际情形:“从根本说来我并未提出任何方法,相反,我只是描述了实际情形。”<24> 何谓描述了实际情形?在笔者看来,这必须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现象学维度来看:伽达默尔强调自己的真正关注过去是、如今也仍然是一种哲学性的关注,亦即关注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或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在我们所想、所做之外和之上,有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25>
另一方面,在提出效果史概念时,伽达默尔也反复强调,自己并非在一种传统诠释学的意义上(作为方法的诠释学)提出效果史的要求。从消极面而言,他并不是提倡历史研究必须发展一种关于效果史的研究——作为一种与理解作品本身的研究相分离的研究;也不是说,效果史必须发展成一门辅助人文科学的独立学科。从积极面而言,效果史原则所提出的对理解的要求,是更具理论性的要求——就如伽达默尔的关注是哲学性的关注、而非方法性的关注一样。或者,效果史原则提出的要求就是一种原则上的要求(效果史原则)或意识上的要求(效果史意识);亦即,我们必须意识到诠释者的理解的历史性,因此也就是要意识到诠释者所试图理解的历史现象总是在对我们发挥着影响(或效果)——这种总是被影响的状况就是诠释者的诠释学状况(hermeneutical situation)。<26> 而这种意识,就是伽达默尔要求的效果史意识(consciousness of being affected by history,或意识到被历史所影响)。<27> 简言之,伽达默尔主张的并非作为方法或学科的效果史(认识论意义上),而是作为原则或意识的效果史(本体论意义上)。
(二)作为方法或学科的接受史
但是,正如Robert C. Holub所揭示的,伽达默尔的作品在接受理论发展过程中颇具影响力,这其实有点讽刺。原因在于,许多接受理论家最想要的,似乎正是前文所述伽达默尔所怀疑的东西,即“一个方法,它不仅是为了用以研究和分析文献、而且是为了获得关于文本的真理;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主要的批判目标是自然科学式的方法对真理和知识的垄断,不过,伽达默尔对方法的攻击也适用于接受理论所做的事情。”<28> 同样地,Mark Knight也指出,源于伽达默尔的学生姚斯的接受史概念,与伽达默尔自己的效果史概念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姚斯的方法论倾向(回到认识论诠释学),亦即姚斯从文学诠释学的角度,描绘了一幅新文学史的方法论框架。Mark Knight解释道,这一点也正是姚斯的接受史理论对注重方法论的圣经研究学者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29>
姚斯的接受史理论确实应用(或挪用)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史,将其从哲学上的原则或意识化成一种方法,进而通过此方法重建一个学科(新文学史)。<30>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方法或学科的接受史完全是对效果史的曲解。一方面,我们将看到,伽达默尔阐述的理解的历史性和效果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也制约了接受史的发展。Robert C. Holub指出,尽管伽达默尔声明自己不主张方法论,但是他的哲学诠释学确实为接受理论预备了土壤;尤其是效果史和视域等概念被姚斯等人在文学理论中频繁地挪用。<31>
另一方面,尽管伽达默尔澄清道,自己的哲学诠释学被他人归入传统的(认识论)诠释学的范畴是一场误会<32>,但如果我们坚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逻辑来描述实际情形,将效果史理论本身视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话;那么必须要说,对效果史的解读,并不只以伽达默尔这个作者的诠释为至高无上的判准。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效果史理论与作为历史主体的接受史理论家二者之间同样是一种对话,而非文本(《真理与方法》)或作者(伽达默尔)的独白(文本与作者并不垄断意义的产生)。如此,接受史将效果史从原则与意识的层面转化为方法与学科的层面,这种挪用虽未必是伽达默尔赋予文本的原意(伽达默尔当然会反对理解的任务是要追寻作者的原意),但无论如何也都是作为历史文本的《真理与方法》一书所产生的一种效果。
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反思19世纪初以来的兰克史学影响下的历史主义范式,以及伽达默尔自己举的效果史例证,本身也(无意地)暗示了接受史学者可以从方法和学科的范式转型的角度推进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方向。更何况,我们在下面具体讨论圣经接受史的时候也会看到,主张接受史与效应史的圣经研究,在提倡方法或学科的面向时,也未必要彻底放弃原则与意识的面向。如果说效果史的方法论化以及伽达默尔对接受史的影响真是一个误会的话,<33> 那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三)文学史中的接受史
现在,我们需要从孕育接受史概念的文学史的视角,来探讨何为文学史中的接受史。上文已经提到,效果史这个词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创造;而接受史这个词则是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姚斯所提倡。<34> 我们先探讨姚斯提倡文学史的接受史转向的缘由,尤其是围绕理解的历史性以及效果史的哲学诠释学对接受史内涵产生的影响,其次再讨论两个概念的异同。
1966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Constance)大学成立,其愿景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在该大学初期聘用的五个教授中,其中一个就是姚斯。姚斯在1967年的就职演讲“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后来收入《走向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一书——实际上成为了接受理论的宣言,而姚斯自然也就被誉为现代接受理论的创始人。<35> 在该演讲中,姚斯批判既有的文学史研究,认为文学史家更喜欢诉诸历史编纂学的客观性理想——这是兰克影响下的历史主义的遗产——即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描绘历史。姚斯指出,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只关心作品的起源所涉及的作者生平状况与历史状况,只关心一个体裁发展的过程,而根本没有关心那些影响作品质量高下的因素,也就是作品的影响、接受以及作品后来的名声。<36> 与他的老师伽达默尔一样,姚斯同样反对兰克史学影响下的历史主义所推崇的对历史书写之客观性的追求。兰克坚持认为,“每个时代是直接面对上帝,而且每个时代的价值并不依赖于发生在其后的事情,而只是依赖于其自身。”因此,历史主义切断了历史的过去和现在,切断了历史的过去的样子与其后发生的事情。<37> 简单而言,若用伽达默尔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在姚斯之前的文学史书写中,历史的实体与历史的效果这两者被隔离开来,对前者的研究毫不考虑后者。
因此,姚斯所提倡新的文学史对既有的文学理论的挑战,正在于重新连接历史的实体与历史的效果。具体而言,姚斯提醒我们,不仅需要通过作品的生产(作者、作品生产之初的社会文化处境以及原初读者等因素)、也必然需要通过作品的消费(后来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来研究文学作品:
如果作品的生命“并非源于它自主的存在,而是源于作品与人之间的互惠交流”,那么这种理解的永恒工作、以及活跃地再现过去的永恒工作,不能限制在单一作品中。相反地,作品与作品的关系如今必须带入到作品与人的交流中,而作品自身的历史融贯性必须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联中来探讨。换言之:文学与艺术只有在拥有以下这个特征才获得其历史,即作品的传递不仅通过生产主体、也通过消费主体——通过作者与公众的交流——来进行。<38>
在此,与伽达默尔一样,姚斯预设了先前的作品及其生产主体与后来的诠释者(亦即消费主体)二者存在对话关系,其诠释学基础就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强调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效果史原则。要理解历史现象,具体而言要理解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同时讨论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只关注文学作品的生产。其中,后来的读者对作品的消费,就是接受史一词中的接受的另一种表达。因此,文学史中的接受史,就是指从作品与读者之间对话的视域,探讨作品发挥影响和被接受的历史。或者,文学史中的接受史,就是指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不同的读者所消费的历史。这里所谓的消费,在姚斯看来并非指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种彻底的读者决定论),而仍然强调作品与读者的互动或对话。接受史的任务,就是通过探讨该视域,重新连接起被历史主义所割裂的关于文学的过去经验与当下经验。<39>
(四)从效果到接受
据以上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姚斯的接受史理论有基础性的影响。但是,既然如此,为何姚斯要使用接受史一词,而放弃效果史一词呢?二者的区别何在?这就要从姚斯对伽达默尔的反思出发。
效果史与接受史这两个概念明显的不同在于,德文效果史是“效果”(wirkungs)与“历史”(geschichte)两个词的合成,而德文接受史则是“接受”(rezeption)与“历史”(geschichte)两个词的合成。“历史”一词保持不变,关键的变化就是与“历史”一词搭配的“效果”变成了“接受”。所以,其中呈现的差异或许正在于“效果”一词与“接受”一词的不同内涵。事实上,单就字面而言,就已经可以看出侧重点的不同。若以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为例,“效果”(或geschichte的另一种翻译,即“影响”)一词,其侧重点是文本对读者的效果(或影响),更强调文本的能动作用;“接受”一词,其侧重点则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更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40> Robert C. Holub早已提出,接受理论的核心争议在于定义问题。最持久的困境就是wirkung与rezeption如何区分。他指出,二者的相同处在于均关注的是作品与读者的互动;而对二者最常见的区分是,wirkung与“文本”相关联,而rezeption则与“读者”相关联。不过, Holub也承认,这样的区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41>
的确,姚斯弃“效果”而用“接受”,源于他对伽达默尔理论的不满。姚斯反对伽达默尔对经典的定义,后者认为经典是自我诠释的。就此,姚斯指出这种对经典本身之力量过于强调的判断,与效果史原则相矛盾;因为读者即便对所谓的经典的理解,也不仅仅是具有复制性(reproductive),而且也是具有创造性(productive)。姚斯进而对伽达默尔的理解概念提出质疑;姚斯认为,伽达默尔只是将理解视为把自己放在传统的过程之中,所以会让理解的创造性功能大打折扣。姚斯认为需要强调理解的创造性,而这种强调也必然包括了批判和遗忘传统(例如经典)。<42> 简言之,在姚斯眼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过于强调经典(或其他的先前文本)的效果(或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在接受经典的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姚斯改用接受史一词,就是要纠正效果史对读者的重视仍显不够这一缺点。
在笔者看来,问题应当一分为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确实有将重心放在强调传统之上的倾向;这也是利科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界定为“关于传统的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tradition)<43>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对话的诠释学,那么伽达默尔即便更强调的是传统对诠释者的效果,但同时他也未完全忽略诠释者对传统的能动接受;伽达默尔自己早就说过,理解不仅仅是“一种复制性(reproductive)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productive)的行为”。<44>
此外,姚斯的接受史概念尽管建基于对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概念的批判,但也丝毫不意味着姚斯就完全走向排他性地强调读者的作用、而忽略文本的作用(这属于激进的读者反应理论<45>)的地步。事实上,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倡的接受史,依然是对话的诠释学在文学史中的反映。在强调读者的接受时,姚斯同样也强调文本的效果(或影响)。这一点从他在行文中常常将接受与影响二词连用可以看出。<46>
这样看来,效果史与接受史以及效果与接受,在伽达默尔与姚斯的作品中,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只是在量上有差异,而绝非质的不同。<47> 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下文中扩展对圣经接受史的理解十分重要。
三、圣经接受史
(一)接受史与圣经
那么,何为圣经接受史?前文提到,一方面,无论是伽达默尔的效果史,还是姚斯的接受史,其中的“历史”(geschichte)一词在德文中的意义已经是“具历史重要性的历史”。所谓某个历史事件之具历史重要性,也总是后来的诠释者(例如史学家)以他的前见对该事件的后来的效果或无效果所作出的判断。换言之,“历史”(geschichte)一词本身就已内蕴着历史现象的效果、影响或接受的含义。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倡导的效果史,指的是这样一条诠释学原则,即在理解历史现象或传统作品时,同时考虑该历史现象或传统作品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效果;姚斯倡导的接受史,指的是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不同的读者消费的历史。同时,效果史与接受史虽不尽相同,但却非质的差异。
在效果史或接受史概念中加上“圣经”作为限定语,而成为圣经接受史一词时,自然受到效果史或接受史原初意义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在既有文献中对圣经接受史一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圣经效果史,因此下文以该词为探讨的中心。根据前面两部分的考察,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关于圣经接受史的初步定义:圣经接受史就是指圣经在不同的时空中产生效果(或影响)、或被不同的读者接受(或消费)的历史。
(二)圣经接受史、历史批判与文学批判
在进一步改进圣经接受史的初步定义之前,我们需要讨论圣经接受史与圣经研究其他相关的方法或子学科的关系。毕竟,效果史与接受史的术语确实是首先由圣经研究学者引入广义的神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瑞士神学家、圣经研究学者Ulrich Luz第一次在他专长的《马太福音》研究(包括注疏与专著)中引入了效果史与接受史的概念,并且一直积极倡导圣经接受史的研究。<48> 接下来,我们要分别讨论圣经接受史与历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文学批判(literary criticism)、诠释史(Auslegungsgeschicht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exegesis)以及后现代诠释(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这四者的关系。
其一,圣经接受史与历史批判。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伽达默尔还是姚斯,他们提倡效果史或接受史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对历史主义的历史思考——追求客观性、不考虑诠释者前见——进行反思。同样地,圣经接受史的产生,也缘起于对圣经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批判的反思。圣经研究中的历史批判,指的是“通过将圣经放在写作时代的处境中,通过探讨圣经如何形成、圣经作者的目的是什么,以尝试理解圣经”。<49> 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历史批判占据了圣经研究的中心舞台,三个世纪的圣经学术主要聚焦于圣经文本的作者、年代界定以及历史背景等研究之上。<50> 简言之,历史批判的任务就是研究者需要秉持客观中立的研究方法,力图寻得文本背后的原初意义(meaning behind the text)。
由此看来,历史批判也是历史主义式的历史思考在圣经研究中的反映。正因为这种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追求,Heikki M. Räisänen才承认,“圣经有什么效果”这个问题——换个经典的说法,即圣经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实际意义(meaning in front of the text historically)——几乎被诠释共同体所遗忘。<51> J. F. A. Sawyer也指出,历史批判造成了圣经本身与圣经在宗教信徒论述中的使用二者的分裂;后者(亦即历世以来在文学、艺术、音乐等之中的圣经诠释)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后期的、无批判性的。<52> 因此,圣经接受史——与其他后批判运动一起<53>——批评历史批判执着于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迷思,挑战历史批判的前设,亦即“文本的原初意义必然是圣经研究的首要目标”。<54> 圣经接受史拒绝区分圣经的原初意义(original meanings)与诠释史上的意义(meanings in interpretive history)。<55> 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效果史的探究绝非附属与补充,而是“从对历史意识的彻底反思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我们总是需要、而非偶尔需要拥有效果史意识。”<56> 因此,上文所述之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姚斯的文学诠释学,为圣经接受史对历史批判的反思提供了诠释学根基。
其二,圣经接受史与文学批判。圣经接受史并非直接针对文学批判而提出。尽管二者均反对历史批判,但它们的任务各有不同。文学批判通常指的是“分析和诠释圣经经卷的意义和结构,将圣经经卷视为文学性的整体”。<57> 换言之,文学批判关注的是文本之中的意义(meaning in the text)。而如前述,圣经接受史关注的主要是圣经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实际意义。<58>
(三)圣经接受史、诠释史与后现代诠释
其三,圣经接受史与诠释史。早在圣经接受史兴起(20世纪后半叶)之前,圣经研究中早已有完备的诠释史这一分支。<59> 在圣经接受史兴起之后,诠释史一般被认为是广义圣经接受史的一部分,或所谓传统的圣经接受史。<60> 按Ulrich Luz的定义,诠释史强调的是在不同神学家(尤其是所谓的正统神学家)的注疏中,圣经如何被诠释的历史;狭义的圣经接受史为了与诠释史相区别,常常指的是圣经在注疏以外的文字媒介(例如证道或文学)与非文字媒介(例如艺术或音乐)中如何被接受(received)和实现(actualized)的历史。<61> Ulrich Luz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媒介的不同。<6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圣经注疏这一个基督教神学的文类早已有之。但效果史与接受史被引入圣经研究后,向圣经注疏注入的新鲜元素,就是在注疏中会罗列诠释史上重要神学家的诠释。<63>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Ulrich Luz的《马太福音注疏》以及Anthony Thiselton的《哥林多前书注疏》,<64> 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布莱克维尔圣经注疏”系列、“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与“教会圣经系列”。这是在引入圣经接受史之前,以历史批判为主导的圣经注疏中很少会囊括的内容。
其四,圣经接受史与后现代诠释。圣经接受史与后现代诠释均挑战历史批判所主张的客观性、中立性以及对文本原初意义的追寻,同时也都强调在文本前面的意义(meaning in front of the text),亦即读者以及不同读者的特定处境对理解文本的重要作用。但是,二者的差别在于,后现代诠释是建构性的(meaning in front of the text constructively),其任务是探讨从读者的处境出发,圣经文本应该(de jure)具有的意义(例如解放神学诠释、女性主义诠释、后殖民诠释);而圣经接受史则是历史性的(meaning in front of the text historically),其任务是探讨从读者的处境出发,圣经文本实际(de facto)曾经具有的意义。
(四)圣经接受史的性质
在前文中,我们将圣经接受史与历史批判、文学批判、诠释史以及后现代诠释等圣经研究的子学科并列,似乎是将圣经接受史当然视为在圣经研究之下、具有独特研究方法的一门子学科。这样的论述,是否只符合姚斯的理论(即作为方法或学科的接受史),而并非伽达默尔提倡的作为原则或意识的效果史?这关涉到圣经接受史的性质问题。
一方面,正如前述,必须承认伽达默尔作为《真理与方法》的作者,确实不打算将效果史变成一个方法或学科,而是保持一种理论上与哲学上的本体论属性。但是,笔者想追问的是,若不考虑伽达默尔的作者意图,《真理与方法》文本自身是否有过暗示,使得主张接受史的姚斯及其后主张圣经接受史的圣经研究学者重新探讨作为方法或学科的效果史具有正当性?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曾再次反思史学书写与史学研究的模式问题。他反复强调,每一种史学观察都以对效果史的有意识反思为其基础,史学书写与史学研究根本无法完全避开效果史研究的领域。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伽达默尔在此举了一个历史编纂学的例子来具体化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后的读者如果重新读1960年的史学家所写成的北美洲爱斯基摩人部落的历史,就会发现1960年所写的这个历史在半世纪或一世纪后一定已经过时了,“因为那时他(引者按:将来的读者)将知道更多的东西、或者更正确地解释原始资料”;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也会看到,在1960年,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这些原始资料的,因为他们是被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成见和不同的兴趣所支配”。<65> 在此,效果史的反思既是一种哲学诠释学的原则或意识,又实际上示范了如何将之应用在具体的史学书写与史学研究中。而这种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一种方法的应用?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圣经接受史研究,正像伽达默尔举的例子一样,其任务就是站在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之后(以及更长时段以后)来探讨曾经受过圣经影响的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圣经(伽达默尔所谓原始资料),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又是如何具体地被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成见和不同的兴趣所支配。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圣经接受史作为在圣经研究之下、具有独特研究方法的一门子学科,即便在《真理与方法》中的效果史那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66>
但是,另一方面,保持圣经接受史内蕴的原则或意识面向,而不仅仅将其化约为圣经研究的一种方法或学科,有助于我们扩大对圣经接受史的理解。当圣经接受史被视为原则或意识的时候,它就不局限于所谓的圣经研究内部,而可以扩展到圣经研究之外,适用于教会史<67>甚至其他历史学科(艺术史、音乐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只要圣经曾在某一特定历史现象中产生过效果、并且留下了证据供我们识别的话。同时,即便是在圣经研究的内部,接受史也可以超越圣经文本形成之后的文本面前的意义之外,将历史批判所探寻的文本背后的意义与文学批判所探寻的文本之中的意义囊括其中。例如William John Lyons尝试以圣经接受史的术语重塑历史批判:比如编修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讨论的是作为读者的编修者(如《马太福音》的作者)如何接受既有的文本(如《马可福音》);再如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讨论的是作为读者的文本抄写员如何接受在他之前的抄本;又如对历史批判具有重要意义的读者群(readership)问题,也正是尝试合理地建构出原初读者(imagined audience)对例如某一封书信可能出现的接受;甚至包括作为旧约读者的新约作者对旧约的接受。<68> 事实上,Ulrich Luz早就指出,圣经本身既是效果史的结果、又是效果史的源头。<69> 如果在本质上,理解是一个效果史事件(伽达默尔)的话,如果“理解就是存在”(海德格尔)的话,那么与圣经有关的原始资料产生之后的效果史就是存在本身——而存在就是我们的本体性规定。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圣经接受史的性质既是一个方法或学科,又是一个原则或意识。
结论
笔者主张,我们要从原则或意识的角度,为圣经接受史下一个足够广阔的定义,同时要从方法或学科的角度,围绕这个定义勾勒一个圣经接受史的研究框架。圣经接受史指的是:圣经文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或文化中,以任何媒介产生的任何效果(或影响)以及被任何读者接受(或消费)的历史。其中,圣经文本从内容上,包括圣经人物、圣经意象、圣经事件、圣经经节、圣经片段、圣经经卷、整本圣经;从形式上,包括圣经的物质形态<70>(例如与圣经有关的媒介技术、可视外观以及文本布局等<71>)。媒介则包括文字媒介(神学论著、圣经注疏、证道、歌词、文学)与非文字媒介(绘画、雕塑、建筑、电影、电视)。效果(或影响)不仅包括积极效果、积极影响,还包括消极效果、消极影响。接受(或消费)包括理解(understanding)、诠释(interpretation)、使用(use)、应用(application)、挪用(appropriation)、再现(representation)、翻译(translation)、滥用(misuse)、曲解(misinterpretation)或转生(afterlife)。读者包括基督徒(神学家、牧者、平信徒;正统、极端与异端)与非基督徒(其他宗教徒、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以及其他社会学身分下(性别、阶级、种族)的读者。
提倡圣经接受史的研究,需要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在当代社会多元主义的公共空间中,从历时性的角度探讨圣经曾经有过的影响和接受。从处境的角度看,世界基督教史、尤其是中国基督教史下的中国圣经接受史也值得进一步研究。<72> James G. Crossley在倡议圣经接受史研究时指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圣经或许就是西方文化(甚至超出西方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汇编,且出现在所有无法预料之处。所以,理解圣经的接受和影响,是理解人类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此,圣经接受史的价值在于,圣经不仅仅是敬虔之人(如基督徒)的活动之所;它也是一扇窗户,让我们透过它来理解成百上千年来的人类。<73>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2>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第2版序言”,载氏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9页;Hans-Georg Gadamer,“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i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From Ast to Ricoeur, ed. Gayle L. Ormiston et 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205. 该引文以汉译为蓝本,对比英译作修改。
<3>中文也可翻译成“效果历史”、“效应史”或“影响史”,在本文不作区别,统一用效果史。
<4> James G. Crossley, 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19.
<5> J. F. A. Sawyer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6> Michael Lieb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e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Hans-Josef Klauck et al.,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Dianne Bergant, C. S. A. and James Dunkly, “Critical Review: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ological Librarianship: An Onl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 (2009): 98–102.
<8> Judith Kovacs and Christopher Rowland, Revelation: The Apocalypse of Jesus Christ (Malden: Blackwell, 2004).
<9> Nancy Klancher, The Taming of the Canaanite Woman: Constructions of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Afterlife of Matthew 15:21–28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3). 其他散见的专著更多。明确以接受史或效果史作为书名关键词的著作,例如:Rachel Nicholl, Walking on the Water: Reading Mt. 14:22–33 in the Light of Its Wirkungsgeschichte (Leiden: Brill, 2008); Víctor Manuel Morales Vásquez, Contours of a Biblical Reception Theory: Studies in the Rezeptionsgeschichte of Romans 13.1–7 (Göttingen: V & R unipress, 2012).
<10> I. Howard Marshall, I Believe in the Historical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43–44; 马素尔,《我信历史上的耶稣》,黄浩仪译,香港:天道书楼, 1988年,第44—45页。
<11> Markus Bockmuehl在提倡新约研究学者应该关注新约文本的效果史时,指出新约效果史的研究意味着新约不仅是“历史上的文献”(historical document),还是“具历史重要性的文献”(historic document)。参见Markus Bockmuehl, Seeing the Word: Refocusing New Testament Stud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65.
<12> Marshall, I Believe in the Historical Jesus, 44. 姚斯曾总结伽达默尔的论点:一个在前的事件,若没有看其后果,就无法理解它;同样,若不考察一部作品的影响,就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参见Hans Robert Jauss,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s of Dialogic Understanding, trans. Michael H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197—198.
<13>“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前有’、先行见到‘前见’与先行掌握‘前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84页。
<14>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et al. (London: Continuum, 2004), 299;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84—385页。该引文以汉译为蓝本,对比英译作修改。
<15> Sinéad Murphy, Effective History: On Critical Practice under Historical Condi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16>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30—331页。
<17>“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7页。
<18>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88页。
<19>伽达默尔在“诠释学与历史主义”一文中也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是:“没有永恒的真理。真理是对存在的揭示,这个存在是随着此在(Dasein)的历史性被给定的。”对历史客观主义进行的批判,就是从这个根基获得本体论上的合法性。参见Hans-Georg Gadamer, “Supplement I: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ism (1965),” in Truth and Method, 526.
<20> Sinéad Murphy指出,西方的谚语所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鞋子中”(put oneself into the other’s shoes)绝非在理解“他人”的时候取消了“自己”的主体参与;相反,“把自己放在他人的鞋子中”意味着“把自己(oneself)放在他人的鞋子中”。参见Murphy, Effective History, 7.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21>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ed. Ormiston et al., 300.
<2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603页。
<23> Hans-Georg Gadamer, “For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Truth and Method, xxv.
<24>伽达默尔,“诠释学与历史主义(1965)”,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诠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5> Hans-Georg Gadamer, “For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xxvi.
<26>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99-301.
<27>利科将其翻译成“暴露在历史效果面前的意识”(consciousness exposed to the effects of history)或“历史效果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efficacy)。参见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305.
<28> Robert C. Holub, 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1984), 36.
<29> Mark Knight, “Wirkungsgeschichte, Reception History, Reception Theo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3 (2010), 139. 另一位圣经研究学者Heikki M. Räisänen也再次重申,伽达默尔根本不认为效果史是一门经验学科;伽达默尔讨论效果史,只不过是要说明,我们总是被效果史的效果所影响,以及告诉我们需要留心传统。参见Heikki M. Räisänen, “The ‘Effective History’ of the Bible: A Challenge to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Challeng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ollected Essays, 1991–2001 (Leiden: Brill, 2001), 265.
<30>同样地,John F. A. Sawyer从圣经研究的角度指出,伽达默尔的效果史在圣经研究中确实成为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参见John F. A. Sawyer, “The Role of Reception Theory,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and/or Impact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the Bible: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an Antonio, Texas, November 20–23, 2004).
<31> C. Holub, Reception Theory, 44.
<32>“显然,我启用具有古老传统的诠释学(Hermeneutik)这一术语,已引起某些误解。”参见加达默尔,“第2版序言”,第4页。
<33> Holub, Reception Theory, 44.
<34>姚斯从1948年开始到1954年,一直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浪漫主义语文学、哲学、历史以及日尔曼民族历史与文化。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思想都影响过他。参见Ormond Rush, The Reception of Doctrine: An Appropriation of Hans Robert Jauss’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Roma: Gregori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35> Anthony C. Thiselton, “Reception Theory, H. R. Jauss and the Formative Power of Scripture,”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5 (2012): 289–290.
<36> 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Brighton: Harvester, 1982), 5.
<37> Ibid., 8.
<38> Ibid., 15.
<39> Ibid., 19.
<40> Ulrich Luz也认为,接受史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而效果史则是从原初事件或文本的角度出发。参见Ulrich Luz, “The Contribution of Reception History to 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Nature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Morgan, ed. Christopher Rowland et al. (Malden/Oxford: Blackwell, 2006), 124.
<41> Holub, Reception Theory, xi.
<42> 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Brighton: Harvester, 1982), 30–32.
<43>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330.
<44>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80页。
<45> Anthony Thiselton指出,姚斯的文学史对读者的强调,让德曼(Paul de Man)认为德国的接受美学等同于美国的读者反应理论。但Stanley Fish、Norman Holland与David Bleich这些更激进的读者反应理论,事实上比姚斯的接受理论更强调读者的主体参与。参见Thiselton, “Reception Theory, H. R. Jauss and the Formative Power of Scripture,” 291. 因此,例如黄保罗也将姚斯的研究归入“读者反应批评”一派,但在该学派中作出两类区分。一类是“极端的读者反应批评学者”,他们坚持“文本的意义完全由读者创造,认为任何确定文本意义的要求都是非法的”;另一类是“占主流的读者反应批判”,他们“还是以文本与读者的相遇为基础,而并不是仅仅强调读者一方”。参见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60—361页。这样看的话,姚斯的接受史显然属于后一派。
<46>例如,姚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都忽略了文学的接受和影响。甚至,姚斯所提倡的美学,并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受美学,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受和影响美学”。参见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18–19.
<47> Jonathan Roberts指出,意义是由文本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在线的这边,文本结束了;在线的那边,读者开始了。参见Jonathan Roberts, “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e Bible, ed. Lieb et al., 8.
<48> Ulrich Luz将圣经效果史与圣经接受史视为同义词,尽管他仍然倾向于使用圣经效果史一词。参见Ulrich Luz, Studies in Matthew, trans. Rosemary Sel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351.
<49> John Barton and John Muddi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Bible Commentary, ed. John Barton and John Muddi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
<50> Sawyer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113–114. 在神学和文学中,19世纪大多数时候的文本-诠释方法的特征通常就是历史主义,即一种纯粹历史的进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神学家而言,对圣经文本进行历史批判研究,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处理圣经文本的学术方式。参见Werner G. Jeanrond,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1), 122.
<51> Räisänen, “The ‘Effective History’ of the Bible,” 263.
<52> Sawyer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114.
<53> Barton and Muddi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2–3.
<54> Sawyer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114.
<55> William John Lyons, “Hope fore a Troubled Discipline? Contributions to New Testament Studies from Reception Histo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3 (2010): 219. 在论及明确以圣经接受史为旨趣的布莱克维尔圣经注疏系列时,主编Christopher Rowland指出,在该系列中,历史批判释经是效果史的一部分。效果史并不是对历史批判释经的补充;相反,二者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无论如何,文本的起源、文本的原初意义、文本对原初读者的效果等均不具有优先地位。Rowland认为,如果诠释的中心不再集中于作者意图,那么圣经接受史就变得格外重要;而作者的地位就变得与那个接受其文本的读者相似。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处于诠释者的位置。因此,文本的转生就是圣经诠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文本的转生指的是读者在圣经文本中找到灵感,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诠释技巧打开圣经文本中的奥秘。文本的转生至少与作者以及原初读者所认为的意义同等重要。参见Christopher Rowland,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Wirkungsgeschichte: Reflections on the Blackwell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and on the Writing of its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an Antonio, Texas, November 20–23, 2004).
<56>“历史学的兴趣不只是注意历史现象或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且还在一种附属的意义上注意到这些现象和作品在历史(最后也包括对这些现象和作品研究的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对那类曾经引发出许多有价值历史洞见的历史探究……的一种单纯的补充。就此而言,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每当一部作品或一个流传物应当从传说和历史之间的朦胧地带摆脱出来,而让其真正意义得以清楚而明晰地呈现时,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种效果历史的探究,这事实上却是一种新的要求——但不是对研究的要求,而是对研究的方法论意识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从对历史意识的彻底反思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参见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385页。
<57> Sawyer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153.
<58> Timothy Beal指出,圣经接受史有助于圣经学术与其他宗教研究进行对话,因为圣经接受史关注的更少是圣经文本之中的意义,更多的是“意义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从圣经文本处产生出来”(how meaning is made from biblical text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参见Timothy Beal, “Reception History and Beyond: Towar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cripture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9 (2011): 364.
<59> Hans-Josef Klauck et al., “Introduct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ed. Hans-Josef Klauck et al.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xi.
<60> Crossley用历史神学一词来指称传统进路的接受史。在他看来,历史神学指的是不同的神学思想家如何诠释圣经文本,问的主要问题是:“诸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或巴特等著名的神学家如何诠释某段经文?”参见Crossley, 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118, 129. 但按笔者的理解,历史神学实际上包含的范围广于诠释史,它实际上还包括了教义史与建构性神学的历史,因此如果将历史神学等同于诠释史,似乎容易起到误导的效果。
<61> Ulrich Luz, Matthew 1–7: A Commentary, trans. James E. Crou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7), 61.
<62> Nancy Klancher认为,旧的诠释史与新的接受史的基本分别在于:前者仍然想要判断出每个圣经文本的原初正解;后者则停止回望文本的起源,开始将文本放在演化中的读者之中,以及放在社会、政治与神学处境及其功能之中。参见Nancy Klancher, “A Genealogy for Reception Histor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1 (2013): 106.
<63> Crossley, 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118.
<64> Luz, Matthew 1–7; Anthony C. Thiselt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65>加达默尔,“第2版序言”,第8—9页;Hans-Georg Gadamer,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205.
<66>事实上,在《真理与方法》的〈后记〉中,伽达默尔承认,“真理和方法之间对立的尖锐化在我的研究中具有一种论战的意义。正如笛卡尔所承认,使一件被歪曲的事物重新恢复正确的特定结构在于,人们必须矫枉过正。”参见加达默尔,“后记”,载氏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第738页。既然“真理和方法之间对立的尖锐化”是伽达默尔有意“矫枉过正”的结果,那么在笔者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效果史的方法面向,即便在伽达默尔那里,也未尝不可。
<67> David P. Parris指出,接受理论提供了诠释资源与洞见,能够提供一个诠释学模型,将释经、圣经诠释史与教会史互相联系在一起。参见David P. Parris, Reception Theory and Biblical Hermeneutics (Eugene: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09), ix.
<68> William John Lyons, “Hope fore a Troubled Discipline? Contributions to New Testament Studies from Reception Histo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3 (2010): 213.
<69>一方面,圣经文本自身就是效果历史的结果,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对该历史的诠释、耶稣的历史、对耶稣进行的最早的文本诠释的结果。另一方面,圣经文本有自己的效果历史,也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会认信的历史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参见Ulrich Luz, Matthew in History: Interpretation, Influence, and Effect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23–24.
<70>这也是Timothy Beal提出圣经接受史需要转向圣经文化史的一个核心要义。参见Beal, “Reception History and Beyond,” 366–367.
<71> Timothy Beal, “Cultural-Historical Criticism of Bible,” in New Meanings for Ancient Texts: Recent Approaches to Biblical Criticis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d. Steven L. McKenzie et a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3), 7.
<72>艾伯林(Gerhard Ebeling)早在圣经接受史尚未兴起的1960年代,就尝试“从神学上界定教会史概念”,即“教会史作为圣经诠释的历史”。参见Gerhard Ebeling, “Church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Exposition of Scripture,” in The Word of God and Tradition: Historical Studies Interpreting the Divisions of Christianity, trans. S. H. Hooke (London: Collins, 1968), 26. Karlfried Froehlich也从教会史的角度阐释教会史与圣经的关系。他相信,对一段圣经文本的理解,不可以停留在诠释该文本的前史(prehistory)以及历史性的生活世界(Sitz im Leben),亦即集中于作者意图;理解必须也考虑到圣经文本的后史(post-history),亦即作为圣经文本自身历史性的范式。他认为,比起圣经学者,艺术史家、文学史家、政治科学家以及教会史学家更想要知道如何将圣经文本的后史作为原始资料来使用。因此,Karlfried Froehlich鼓励从圣经诠释史的角度撰写教会史。参见Karlfried Froehlich, “Church History and the Bible,” in Biblical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udies in Honor of Karlfried Froehlich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Mark S. Burrows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9, 11.
<73> James G. Crossley, “An Immodest Proposal for Biblical Studies,” Relegere: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Reception 2 (2012): 164, 172.
(作者为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神学研究院中文部副主任及基督教研究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华人基督教史、加拿大基督教史和数字人文。)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6期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基督教”,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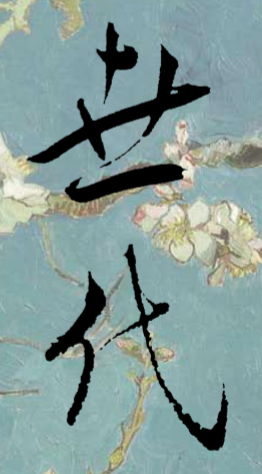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