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油画(1921年)作者:李铁夫(1869—1952)。来源:维基百科]
孙中山(1866—1925)常被尊奉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他领导改组的国民党,在中国南方建立了政权。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及其与早期革命活动的关联已为人熟知,然而在他人生后期,宗教与政党意识形态对其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在当今学术研究中相对较少受到关注。从他在1920年代发表的充满感染力的演说和著述可以看出,孙中山为后来党的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换言之,那种后来在西方冷战时期被称为“洗脑”的“思想改造”,其来有自。孙中山早在他试图将宗教热忱用于党国服务的努力中,就已经初步体现了这一理念。
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性考察孙中山对“感化”(意为改造或皈依)的概念化过程,来剖析其政治宗教性。所谓政治宗教性,正如学者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和宗树人(David A. Palmer)所定义的,是指“国家的神圣化与治理的道德化”<1>。本文并不试图评判这种方法的心理学有效性,也不将“感化”视作纯粹的宗教现象来研究。相反,本文将着眼于孙中山对“感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包括其中所涉的观念、体系与实践——孙中山正是在构建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为了掌握这股力量,孙中山借鉴苏联革命与宣传的模式,将宗教的献身精神予以政治化。这种由党国对“感化”所作的独特界定,标志着20世纪中国政治宗教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有关“感化”的研究概述
当孙中山引入“感化”一词以强调通过民众政治来改变国家所需的思想忠诚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几十年后,西方会因为一种貌似“洗脑”了中国的特殊精神催眠法而陷入恐慌。随着中美关系从二战迅速转变为韩战的对峙,这种迷惘或许可以理解。此外,精神科医生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 Lifton)在1950年代对中共“思想改造”运动之手段与效果所作的大量研究,虽然受限于他所处时代的关切,却也保存了其受访者的宝贵经历。<2> 而那些同情中国共产革命的人,也不怀疑“思想改造”系统改变人心的效能——他们只是认为这种制度是为了让人们将旧习换成新风尚的必要之举,且相较于斯大林苏联血腥清洗是一种更人道的改造方式。<3>无论持何种立场,人们大多认为这种思想改造属于1949年后毛主义的产物。
这些历史和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重新被审视。当时在两个重要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首先,与“感化”一词密切相关的是关于20世纪初中国刑罚体系的开创性研究。冯客(Frank Dikötter)等人的研究利用此前未曾使用过的资料,拓展了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律司法体系的认识。<4>这些研究指出,“感化”在当时起到了刑罚体系指导原则的作用,强调了在改造过程中由国家主导的道德感化层面。<5>
另一个方向的研究,虽未明确提及“感化”一词,也确认了在中共执政前的中国,各种思想改造工程的历史延续性,只不过这些研究侧重于国家建设和政党意识形态。例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试图解构党国对中国民族的话语垄断;倪睿思(Rebecca Nedostup)认为,国民党政权及其种种国家建设与其所整治的宗教一样“迷信”;高华在其有关革命圣地延安的著作中则揭示,“造就新人”是中共崛起的重要因素。<6>
尽管这两类研究都把通过制度化手段改造人心的民族大业追溯到了清末民初,但前者聚焦于针对囚犯群体的刑罚体制,而后者关注党国对其他社会力量的规训,较少考虑宗教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缺,强调“感化”一词作为一种早期且成熟的政治宗教实例,在国民党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居于核心地位。 “感化”一词带有明显的宗教意涵,早在1920年代南京政权建立之前,孙中山作为其政党意识形态的设计师就已经运用了这一概念。对这一关键演变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党派的扩张,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不断增设各种管制性机构来塑造国民。
当孙中山在1910年前后首次使用“感化”一词时,它已经具有两种清晰且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含义——宗教皈依和社会改造。在19世纪90年代末之前,“感化”一词在近代中文报刊中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用法。1869年,《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the Church)刊登了一篇短文,劝勉基督徒“祷主感化,兴旺教会”。<7>该报更名为《万国公报》后,刊登了一篇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中国基督徒领袖陈鸣鹤合著的长文。这篇文章以宗教感化为核心,指出“信耶稣能感化人之性情……作为,使人救普世不惜其力”<8>。 在同期的《申报》中,“感化”一词在大众层面的宗教涵义也屡见不鲜。<9>
随着改良思想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达到高潮,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在众多提倡变法的报刊中,《时务报》最具影响力,其主笔正是维新领袖梁启超(1873—1929)。该报之所以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海外新闻的广泛报道。例如,该报邀请了古城贞吉(Kojo Teikichi)主持日本新闻专栏。他所翻译的大量文章将许多来自日本的新名词引入了汉语。<10> 这些译介的新闻中,就包括日本筹建“感化学校”的计划。“感化”的这一新用法代表了一个西方概念与实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将“感化”视为一种处理罪犯的手段,相应的“感化院”则作为一种教养院式的设施。在这篇文章中,古城将此类感化学校描述为改造“孤儿罪犯者”的教养中心,以便他们在出狱后不至于重蹈犯罪覆辙,而能够学习“人生当务之事,将使渐得衣食之计,为社会之良民也”<11>。另一家维新派报纸也提到了设立感化院,旨在“化莠为良,导邪致正”。<12> 将“感化”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改造形式,本身就是晚清维新运动的标志特征之一:一方面憧憬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以明治日本为楷模。<13> 尤其在日本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胜后,中国普遍认为日本已经证明了其工业与军事实力。日本在语言文化上与中国的相近性,也吸引了许多中国维新者前往取经,以图振兴本国。
诚然,这一传入的“感化”愿景有强烈的西方现代性特征,但仍然经过了中国本土的理解和消化。职业技能培训或启蒙教育固然是感化罪犯所必需的,然而要彻底解决犯罪问题,则需要通过一个更为宏大的过程,从根本上重塑个体的道德观念,实现真正的自新。<14>“感化”有别于20世纪之交诸多社会改良方案,正是它从制度上对感召力的运用,以伦理教化和道德改造为中心。冯客指出“感化”是民国时期刑罚体系的“核心价值”,意指一种制度化、由国家主导的机制,通过榜样示范来感化那些失足者,使其悔过自新。<15>
因此,宗教在各类感化环境中深度介入道德教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奉天省,各监狱发放了佛教书籍,教诲师在集体讲课时鼓励犯人进行“宗教式静思”,希望佛教诵念能够引发他们的忏悔和改过。<16>在浙江定海(邻近佛教圣地普陀山),县监狱邀请了一位退隐的僧人担任教诲师,他在讲堂内悬挂的菩提达摩画像前敲钟诵经,使监狱俨然变成了一座寺院。<17>浙江省首席检察官陶思曾(1878—1943)本人亦为佛教居士,他对定海监狱的佛教感化仪式印象深刻,遂于1922年初迅速推动在浙北大部分县监狱中利用佛教教义来改造犯人。他甚至指派了一批巡回的佛学教师定期赴各狱宣讲。他们大多教授简化的净土宗教义,常带领囚犯诵念《大悲咒》,并引导其讨论和反思自身的因果报应。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佛学感化”,是将佛教皈依紧密融入刑罚改造体系的一种尝试。<18>出于类似促人悔改的逻辑,一些基督教团体(如各教派教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也被鼓励进入北京、山东、奉天、江苏等地的监狱开办讲座,甚至传教,以推动“惩戒与感化”的目标。<19>
这些举措凸显出以道德提升为基础的改造式监禁理念。在这种理念下,教育、惩罚与宗教往往融为一体,其目的在于改变个体的内心,使之重新与正当的社会价值观相契合。也正因此,在这些公共机构中所推广的“宗教”往往变得更加折衷和功利。例如,北京第一监狱的讲堂墙上悬挂着五位“大导师”的画像——“孔子、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以及英国狱政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1726—1790)”。<20>这种务实的作法与孙中山的思路如出一辙:他看重的是“感化”在功能上的效用,而非其教义渊源。
除了20世纪早期的监狱,体现感化精神的民间机构——感化院——也相继涌现。1908年在安徽设立的一所感化院就是一个早期例子。该机构以“列国之成规”为蓝本,附设于省城的一家工艺厂,招收“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游荡及乞丐……以及犯轻罪以下之幼年子弟……设伦理各科……”<21>。其宗旨同样是改造少年犯,使之获得一技之长,将来不再步入牢狱。总体来说,早期“感化”的制度实践形态是灵活多样的,既包括官办刑罚体系,也涵盖更具教育意味的感化院。后一种形态应代表1910年前后多数的感化院。宗教在这些民间感化机构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一个实例是北京西郊香山的感化院——该院是在1922年司法部颁布《感化院暂行章程》后建立的。<22> 该感化院院长熊希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晚清维新人物,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居士。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多个政府职务,曾出任1913—1914年“第一流内阁”的国务总理。该院的教育课程以佛学为中心,并经常邀请德高望重的僧侣来担任客座讲师。<23>继熊希龄之后,王一亭和蔡香孙等社会名流也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组织了感化院,得到宗教界的明确支持。<24>在1922年至1928年间,特别是在北伐前后,出现了一波新建感化院的高潮。<25>
然而,这种民间倡议并未持续多久,就被国民党收编,并在对抗中共的意识形态前线被赋予了新用途。要理解这些国家层面的感化工程如何成型,需要历史性地审视这位党领袖对“感化”的概念化,以及这一概念在新的权威话语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孙中山早期关于感化与宗教的思想
总体而言,孙中山对“感化”的概念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他在约1912年至1919年期间对该词的早期使用较为泛化,并与儒家的治民教化思想一脉相承。然而在1919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超越了儒家话语,将“感化”视为一种对革命的皈依,明确将其与宗教传教及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将“感化”与宣传工作结合起来,提倡将其作为革命斗争的关键手段,并敦促本党党员皈依革命,成为革命的“信徒”,以便去感化整个民族。
与此同时,由于宗教概念与意志力及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孙中山对宗教的理解与感化话语的兴起密切对应,从最初的官方提及,到策略性借用,最后演变为革命性的敌意。他首次大量使用“宗教”一词,集中在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提出了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离的原则。随后在1918至1923年的过渡时期,他更加认识到宗教的力量,并将其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到1924年底,孙中山将“感化”与党的宣传相融合,对宗教的描述越来越符合列宁式的批判,将宗教视作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为了实现他用革命意识形态改造国家的目标,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宗教可能已经失去了其政治价值。
孙中山早期对“感化”的使用,大致延续了儒家道德教化的传统。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基础:第一,认为人性本善,因此能够通过道德修身达到完善。其次,这种道德完善(或社会秩序)的潜力使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大众教育成为必然。这一责任最终由帝国政府承担,并由儒家士绅辅助完成。<26>
1912年1月,在民国成立不久后,孙中山致电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鼓励他通过万国改良会(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积极进行反鸦片运动,“望诸君子热诚诱导,以社会之感化力补其缺憾”。<27> 接下来的几年里,孙中山对“感化”的用法相对灵活,但总体上仍在儒家传统范围内。他曾指出海外华侨应被“感化”而拥护共和,反对党成员也应被“以德感化”,如同历史上中原地区用汉语“感化”边缘族群一样。<28>
孙中山早期对宗教的观点始终基于互不干涉的原则。他坚信,正因如此,信徒才能在宗教信仰上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一时期,每当他承认宗教在道德教化上的力量时,其回应——与后来的积极调用不同——只是宽泛地鼓励爱国热情。1912年3月回应佛教支持者时,孙中山明确规定政教之分是临时约法所承诺的宗教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他赞扬佛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国家则承诺给予“不稍吝惜”的保护。<29>这种宗教自由和平等的措辞,也在孙中山向北京伊斯兰教团体的演讲中得到呼应。<30>
同时,在向基督徒听众更为热情的讲话中,孙中山一再将宗教与道德及广义的爱国责任联系起来。1912年4月参加基督教欢迎会时,他肯定外国传教活动对中华民族的积极道德影响,尤其是推动了“纯净之爱国心”<31>。两周后,在类似场合中,他进一步指出“兄弟姊妹”同时拥有“信徒”与“国民”双重身份,呼吁基督徒们既要“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32>。对此,孙中山可能视宗教的道德功能与儒家道德教化实际等同。
这种假设赋予了宗教一种补充性的角色:“凡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之”<33>。如此理解宗教明显带有现代主义色彩,即由现代国家所核定,并通常以西方启蒙后的基督教文明模式为规范标准。<34> 正是这种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文明,使他确信宗教对政治的辅助角色(甚至优越性)出自宗教的“富于道德” <35>。晚期的孙中山对此则不再乐观。
党化宗教以党化国家。随着192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高潮的到来,基于传统教化的善举对于革命者而言已远不足够。儒家教化实践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信仰的内化。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不识字的基层群众,通常只要在儒家士绅及宗族的监督下遵守特定仪规,以表明对儒家教义和制度等级的服从。<36>即使精英阶层试图强加统一的信仰,只要有一个正统权威中心,个体层面的内心统一往往并不重要。
然而,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者不满足于仅仅“风行草偃”,而是力求唤醒每一个中国人进入革命议程。他们不仅将中国民众视作“一盘散沙”,而且视为一张空白纸。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再是道德完善或偶尔的爱国火花,而是“谁来控制画笔”的问题,赢得政治斗争的一方将能够通过大众灌输,把人民涂上特定的颜色。<37>自此,孙中山对宗教所剩的尊重变得高度功能化(即强调人格改造),且与激进的“感化”观念紧密结合。
在这一后期用法中,“感化”与“党化”国家,即党权对社会的集中与扩张,紧密相关。建立教化型国家的关键不再只是告诉人们应知的内容,而是说服他们需要改变,且只有党才具备实施这种正确改变的资格。这种党化倾向最早体现在孙中山与戴季陶1919年关于社会问题的对话中。孙氏以精英主义的口吻,将“教训、指导群众”比作驯马与猢狲。<38>当时孙氏正忙于重组国民党并准备北伐,他还鼓励革命领导者以迁就群众的动机、兴趣和知识的方式唤醒(感化)他们,而不仅是单向灌输精英知识。其假设显而易见:革命者若要彻底重塑社会而非简单改革,必须找到方法来训练并动员群众。
为了大规模公开动员和改造群众,孙中山从两个看似对立的来源得到启发:宗教传教和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这两者在鼓舞孙氏政治议程上密切相关:前者体现坚定献身与皈依的力量,后者展示了以世俗政治改造人民的可行性。孙中山毫不避讳地结合这两种来源,推动党宣传教义,先党化宗教再党化国家。
鉴于孙中山与宋耀如等中国基督教现代派人士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革命中基督徒的广泛参与及他自身受洗的经历,他熟悉当时在华传教事业,后者涵盖卫生改革、教育、新闻、妇女权益、城市规划等领域。<39>这些基督教社会事工同时也激起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怀疑和敌意,认为其侵犯国家主权,与世俗议程竞争。<40>对孙中山而言,他看重宗教并非出于宗教本身,而是敬佩其强大的意志力——传教士的献身与信徒的自我牺牲。
这种对宗教的解构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有所体现,信中孙中山与其子讨论了阅读问题。为了鼓励孙科广泛阅读,孙中山赞扬了一本名为《宗教破产》(The Bankruptcy of Religion)的书籍,并在自己阅读后,推荐给家人和朋友。<41> 孙中山说,这本书“算为超绝”,“其学问考据,比White氏有过之无不及”——这里指的是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的《基督教王国中科学与神学之战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42>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充满现代主义乐观的作品,夸耀科学从神学束缚中所得的解放。
宗教既已被祛魅,被拿来与其他价值体系相提并论,从而为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建构所用。关于党员对领袖的个人忠诚,孙中山在1920年强调了其对革命事业的必要性——他将自己的“主义”与儒教、基督教、佛教甚至进化论并列进行比较。逻辑很简单:正如每种“主义”各有其代表人物一样,“我这三民主义……也可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43>。换言之,无论党内同志对革命事业多么热忱,这份热忱首先都要被转化为对孙中山本人主义的忠诚。
一年之后,孙中山在对本党同志谈及感化的另一场讲话中,告诫他们要用“革命主义”去感化广西的同胞,以“道德真理征服他们”。他表示,如果革命党人能够将这种主义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宣传开去,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被感化,整个广西都将知晓此主义,从而标志着革命党人的坚实胜利。<44>这种劝诱皈依的逻辑在两年后孙中山的另一场演说中再次出现。他在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强调,每位党员每年应当“感化”十人入党,如此一来
“再过一年两年以后,便是以十传百,百传千,推广到全国,那就是全国的人心,完全被本党所感化……就是本党革命成功之日。”
对孙中山来说,被“感化”加入本党就等同于“改造国家”,而这又等同于“根本改造民心”。<45>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沿着宗教的思路,对党内的“感化”实践作出了进一步阐释。1921年党内讲话一个月后,孙中山在桂林向革命将士们阐述军人精神。其中,他区分了三种“仁”:“救世”、“救人”和“救国”。在这三者中,他将“宗教家之仁”与“志士爱国之仁”相比较,指出两者都奉行“舍身”的原则——孙中山认为两者“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在谈及感化时,孙中山解释说,中国的佛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屡遭迫害而存续下来,正是因为信徒们敢于舍生忘死,得以“宣传其主义,占有强大势力”。正如宗教信徒能够“不稍退缩,盖其心以为感化众人”,爱国志士也应当“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46>换言之,爱国志士就是民族国家的传教士。
两年后,孙中山在一次党内讲话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宗教传播力量的钦佩。他把孔子、佛教徒和基督徒的事业都概括为“宣传”两个字。孙中山声称:“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与此同时,孙中山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应当比宗教信仰更强大:
“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近于空虚;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有凭有据……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
为了追求比传统方式更强大的改造力量,孙中山要将宗教皈依中的教条部分剥离,只保留其中的献身精神和传教技巧。在他看来,“感化就是宣传”。<47>
拆解宗教使之服务于党的宣传——即党化宗教——的工作已在推进。这也许解释了孙中山此时期在广州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上的演讲为何已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与1912年的演说相比,孙中山此时自称“国民党领袖”,并称这些青年会学生是“我们想救国的党人”所欢迎的。基于这一政治构想,在孙中山看来,基督教青年会不过是通过“体育、智育、德育”而“改良人类来救国”的另一种有益努力。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加入青年会获得“道德进步”时,这种救国努力就变得更加有效——同样体现出一种劝导人们皈依的模式。<48>
然而,既然革命者已经表现出如此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孙中山甚至举出两位既是青年会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的革命烈士——为什么革命仍未完全成功呢?孙中山将其归因于民众对革命理解的不够,而这又源于宣传的不足。国民党尚未具备青年会那样的“救国的能力”,即国民党欠缺如青年会“在二十二省之内,都有很完备的机关,宣传你们的主义,使全国青年子弟,明白你们救国的道理”。孙中山不无竞争意识地总结道,“如果国民党有青年会的完全组织······民国当老早成功了。”<49>
青年会的事例并非孙中山首次领悟到政党政治必须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早在俄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孙中山就发现了一个世俗化、政治化的宗教皈依类比。在1920年的两次演说中,孙中山提及“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称其由此产生了“好风气”,“则他国必受感化”。<50>随后,孙中山勉励广东的革命同志仿效俄国榜样,通过“宣传”来同样感化中国其他各省,但不能靠“空言”。他号召国民党“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之成为其他省份改良派和守旧派所瞩目的“极大的文化宣传”。<51>
孙中山认为,苏俄模式对借助感化力量来强化军队更加具有启示意义。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对军事将领和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使人心归向“革命主义”。<52>对于军中将领,孙中山勉励他们向士兵传播“革命主义”,将其转变为“革命军”,使之能够“替‘革命主义’去牺牲……同心协力去定中国”,因为据孙中山所说,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拿主义来感化全国”的方法。<53>而对于本党党员,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要以这种“俄国方法”为榜样,认为这与国民党感化民众的理想一致。他鼓舞听众道:“我党兵力虽弱于人,惟主义则高尚于人,久为国人所信仰……苟我党员能……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54>毕竟,苏联的军队甚至能够感化外国军队,那么中国仿效苏联模式就没理由不能去感化国内的敌人。
在孙中山看来,与宗教传教相比,俄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革命取胜范例:将党员变成真正的信徒,然后将整个国家皈依于他们的“革命主义”。到了1924年1月孙中山讲授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时,他把宗教首先视为一种能使族群凝聚的向心力量。这种向心力虽然强大,但与“血统、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一样,被孙中山视为“天然进化”的结果,对革命议程未必有直接助益。<55>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本着武装与宣传力量并举的精神,在广州的国民党宣传讲习所开学典礼上,对“感化”的重要性作了最后的详尽阐述。<56>在这里,孙中山将“感化”置于中心地位——“军官学校是教学生用枪炮去奋斗,这个讲习所是教学生用言语文字去奋斗”,并以“感化民众”为最大目的。孙中山对这些学员的要求超出了对一般“宣传”的理解。首先,他们所接受训练的宣传工作不仅是向人们传授三民主义的知识,而是真正去“感化”民众,使他们能够“心悦诚服”。其次,孙中山指出,“感化”他人的途径并不在于个人的口才,而有赖于宣传者自身的“至诚”,正如古人说:“至诚感神”。因此,“至诚”意味着讲习所里的“同志们”不仅要“诚心为主义来宣传,要以宣传为终身极大的事业”,还要“牺牲世界一切权利荣华,专心为党来奋斗”。换言之,为了感化整个国家,党的宣传者必须首先采取近乎宗教苦修式的生活,先让自己成为革命的“皈依者”。这种“革命的禁欲主义”,即高万桑和宗树人所说的20世纪中国政治宗教性的第三级,并非起源于共产延安——因为此时孙中山已着手“创造一批肯为本党事业牺牲自己的新人”。<57>
正是在这篇简短演说中,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关于感化与党宣传思想的成熟形态——其中既未提及宗教,也未提及俄国。他已经摈弃了之前所借用的支架。孙中山在宣传讲习所的演讲后数周,政府即颁布政策,禁止宗教领袖参加农民协会或报考公务员。同期被剥夺此等资格的还有“有田地百亩以上者”、“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吸食鸦片者”、“有精神病者”等。<58>在党看来,这些人都属于危害国家救亡的人群。顺应新近掌握的列宁主义反帝话语,孙中山最终将宗教斥为“无所不至,饮心刺骨”的侵略,认为其“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从而导致了义和团这一“国耻”。<59>
孙中山的制度遗产
1924年,孙中山已准备好率领他的皈依者们发动一场感化并拯救整个国家的圣战。然而数月之后,他在北京的猝然辞世,使得其革命事业陷入了停滞和混乱。从长远来看,孙中山依靠思想宣传和党领导军队相结合来感化中国的宏愿,最终被毛泽东在掌控中共和红军的过程中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孙中山关于“感化”的宏大设想在国民党及社会中也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1927年,国民党积聚了足够的政治和组织力量,在南京建立了政权,随即开始将民间发起的感化事业收归国有。有人提议在江苏再办一所感化院,但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予以驳回。时任司法部长蔡元培的解释是:“感化院查系狱政之一种,似非私人所能组织。”<60>于是同年,江苏感化院由省政府创立并管辖,从而终结了感化院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形态。<61>
国共分裂前后,感化院的政治用途又有了新的发展。1928年湖南设立感化院——这一次由省级国民党党部而非省政府创办——“感化”的目标被更为细化。成立大会称这一机构是“吾国创举”,其目的是感化那些抱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让他们“鉴于已往之事实,而乐于悔过自赎”。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仍将继续,但“一般受其愚弄之农工群众青年学生”应当被给予“觉悟自新之机会”。<62>换言之,在这个新的感化机构里,改造人的逻辑不变,但对象变成了意识形态犯。
一旦被收容,其中的中共党员必须坦白自己的思想叛逆,并被感化引导回三民主义的轨道。据该机构的一份公告,“受感化人”将依据其思想犯错的严重程度接受三种层级的感化管制:最严重者关入“禁锢感化”区,较轻者实行“约束感化”,而自动投诚者则每天在“自由感化”区接受强制教育。其目标在于让这些“迷误者”持续接受训练,并希望在每期三个月结束时,他们能够通过一次“思想行为总审查”,并获得“自新证书”后释放。<63>由此可以看出,在新政权眼中,那些被视为对强国无用的人,不再是旧时的少年犯或乞丐,而是那些被认定以共产主义破坏民族革命的“思想土匪”。
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显示,它与孙中山最后那场决定性的感化演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那场演说写于此湖南感化院成立前仅四年。孙中山对于国共分裂以及中共党员被打为“阴险”或许会感到遗憾,但这份文件的措辞却呼应了他本人的坚定信念:凡在思想上偏离正轨者都需要接受“感化教育,使之觉悟自新,信仰三民主义”。该感化院院长称自己“铲共早具决心,爱人尤属夙愿”,因此自视为一名以“至诚”精神“服务党国”的皈依者。倘若孙中山看到自己在最后的感化演说中反复强调的“至诚”一词被如此引用,不知他会作何感想。无论如何,他本人确实与这类感化院的兴起有直接关联。该感化院的官方刊物以孙中山的名言“感化就是宣传”为座右铭,每期刊头都刊载孙氏遗像及遗嘱,宣扬他的三民主义是“一条独一无二的生路,离开了这生路,便入了死路”。<64>在孙中山逝世三年后依然存在如此炽烈的意识形态忠诚,也许说明孙中山要感化全中国的愿景在国民党内部并非完全无人继承。
结语
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已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短兵相接。与此相应,“感化”的理念及其制度体现,在党国的垄断之下,被赋予了一个大为收窄的用途,即专门用于改造政治犯。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化院作为一个党政干部以笔墨为武器展开斗争的意识形态战场,或许正实现了孙中山在其1924年关于将感化视为革命宣传的演讲中所发出的号召。
“感化”在近代中国的概念和制度演变,以及最终被党义垄断的过程,正反映出时代的发展模式。“感化”自始就宣称道德提升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然而这种关联曾一度有着多种不同的诠释。宗教的、道德的以及现代化的途径常常交织在一起,对道德改造、个人行为及其带来的社会层面效益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定义与联系。然而,随着192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和党国体制的兴起,个人自新被越来越多地置于国家层面加以理解。革命党派不再满足于以传统且相对灵活的方式感化民众——他们现在积极寻求动员整个民族,以“觉醒”并“感化”全国民众,将之改造成一个整体性的“国民个体”。政治上的救赎(通常被界定为对党的忠诚)开始垄断道德转化的内涵,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切真情实感。个人的政治异端成为新的需要忏悔的罪过,而革命则成为新的救赎。在孙中山思想中结合了宗教与苏俄模式的关键枢纽——“感化”——中,我们看到了革命宣传即将兴起的一个早期范例,而这场革命宣传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
<1>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2011), p. 168.
<2> 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 Psychiatric Evalu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1 (1956), pp. 75–88; 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1961). 亦参见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1951);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The Story of the Men Who Defied It (New York, 1956).
<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The Classic Account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Communism, rev. ed. (New York, 1994); Harriet C. Mills, “Thought Reform: Ideological Remolding in China”, Atlantic Monthly, 204 (1959); William Hinto,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 1997).
<4> Frank Dikötter, Crime, Prison and Punishment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2002); Xiaoqun Xu, Trial of Modernity: 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01–1937 (Stanford, 2008); Jan Kiely, The Compelling Ideal: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rison in China, 1901–1956 (New Haven, CT, 2014).
<5> Dikötter, Crime, Prison and Punishment in Modern China, pp. 47–48, 108; Kiely, The Compelling Ideal, pp. 20–23, 34–41, 239–247.
<6>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1995);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1996);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200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华,“新人的诞生”,载高华主编,《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7>“祷主感化兴旺教会”,《中国教会新报》第48期(1869年),第4—5页。这是笔者研究中发现“感化”一词最早的用例。
<8>李提摩太、陈鸣鹤,“论信耶稣感化人”,《万国公报》第344期(1875年),第16—19页;第345期(1875年),第24—26页。
<9>参见“论传教源流辨”,《申报》第1期(1874年);“梦乞救生”,《申报》第3期(1875年)。另有儒家传统中劝善之例,参见“刘松岩中丞德政记略”,《申报》第3期(1875年)。
<10>陈一容,“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历史研究》第1期(2010年),第99—115页。
<11>古城贞吉,“日本拟兴感化学校”,《时务报》第24期(1897年),第24—25页。
<12>“日本置感化莠民学校”,《知新报》第62期(1898年),第14页。
<13> Kiely, The Compelling Ideal, pp. 12–15. Kiely指出,中国的情况与当时国际监狱改革以及日本专家小川茂次郎有密切关联。
<14>同上,第18—20页。中国狱政改革家沈家本在其历史研究中,通过将“感化”视为周代“仁政”理念的内涵之一,赋予其文化正当性。
<15>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p. 48.
<16>同上,第108、111页。民间道教劝善书常被列入官府许可的书目之中。
<17>同上,第109、110页。
<18> Kiely, The Compelling Ideal, pp. 138–140.
<19>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pp. 71, 109.
<20>同上,第71页。
<21>“安徽感化院之创立”,《东方杂志》第5卷第9期(1908年),第111—112页。
<22>“感化学校暂行章程”,《司法公报》第160期(1922年),第83页。
<23>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pp. 174–175. “香山感化院致道戒法师函”,《海潮音》第10期(1922年),第4页。
<24>“上宝感化院近讯”,《申报》1926年11月21日;“僧界感化院已开办”,《申报》1928年6月11日;“感化院祷告的功效”,《同文报》第1229期(1926年),第8页。
<25>王才有,“高墙内的‘派系’轮替”,《民国档案》第3期(2016年),第86—101页。
<26> Goossaert an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pp. 33–36.
<27>孙中山,“复万国改良会丁义华勉协助禁烟函”,载《国父全集》第4卷(1912年),第189页。全文可见:http://sunology.yatsen.gov.tw
<28>孙中山,“心坚则不畏敌”,载《国父全集》第3卷(1916年),第178–181页;“批答华侨某同志对反对党化须以德感化”,载《国父全集》第6卷(1916年),第128页;“建国方略”,载《国父全集》第1卷(1919年),第369—373页。
<29>孙中山,“复佛教会论信教自由书”,载《国父全集》第4卷(1912年),第250—251页。
<30>孙中山,“五族人民平等五族宗教亦平等”,载《国父全集》第3卷(1912年),第86页。
<31>孙中山,“外人来华传教增进道德观念”,载《国父全集》第2卷(1912年),第447页。
<32>孙中山,“基督徒应发扬教理同负国家责任”,载《国父全集》第3卷(1912年),第50—51页。
<33>孙中山,“宗教与政治”,载《国父全集》第3卷(1912年),第132—133页。
<34>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pp. 3–10.
<35>孙中山,“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不及”,载《国父全集》第3卷(1912年),第75页。
<36> James L. Watson, “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1993), pp. 80–103.
<37>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 19.
<38>孙中山,“与戴季陶关于社会问题之谈话”,载《国父全集》第2卷(1919年),第524—526页。
<39>舒波,“孙中山与基督教”,《民国档案》第1期(1997年),第69—76页。
<40>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见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67–1927 (New Haven, CT, 200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Daniel H. Bays, “A Chinese Christian “Public Sphere”: Socio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Urban Middle Class Protestant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Kenneth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ed.)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Ann Arbor, MI, 1997), pp. 101–117.
<41>孙中山,“致孙科谈读书函”,载《国父全集》第5卷(1918年),第78页。该书作者应是约瑟夫·麦凯布(Joseph McCabe,1867—1955),曾为天主教神父,后成为世俗主义代言人。
<42>怀特的著作使他成为宗教与科学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观点大多被当代学术界所否定。见 David C. Lindberg and Ronald L. Numbers, God & Nature: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Berkeley, CA, 1986), and David B. Wils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Gary B. Ferngren (ed.) Science & Religio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2002).
<43>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0年),第215—219页。
<44>孙中山,“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1年),第269—272页。
<45>孙中山,“党员不可存心做官”,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46—352页。据一个月后孙中山的另一篇演讲,他运用相同的“传教宣传”逻辑,提出了更大胆的数字。见“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64—371页。
<46>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1年),第281—306页。
<47>孙中山,“国民党奋斗之法宜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92—401页。
<48>孙中山,“国民以人格救国”,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52—361页。
<49>同上。彼时,基督教青年会(YMCA)以“人格救国”的改良口号著称。参见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CT, 2010).
<50>孙中山,“建设广东为全国之模范”,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0年),第220—221页。
<51>孙中山,“统一中国须靠宣传文化”,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0年),第220页。
<52>孙中山,“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71—379页;“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3年),第379—384页。
<53>孙中山,“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54>孙中山,“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
<5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载《国父全集》第1卷(1924年),第3—12页。
<56>孙中山,“语言文字的奋斗”,载《国父全集》第3卷(1924年),第479—482页。此篇短文中“感化”一词共出现十一次。
<57>引文改写自Goossaert an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of Modern China,第169页。原文为:“Third and even more intense was revolutionary asceticism, which aimed to create a new race of humans who would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58>孙中山,“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宣言”,载《国父全集》第2卷(1924年),第153—155页;“考试条例”,载《国父全集》第9卷(1924年),第434—447页。这里所列“宗教领袖”类别,包括神父、牧师、僧人、道士、尼姑与巫师。
<59>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载《国父全集》第2卷(1924年),第163—167页。
<60>蔡元培,“江苏感化院系狱政之一种”,《司法公报》第13期(1928年),第70页。
<61>“苏省感化院章程”,《申报》,1928年6月18日。
<62>袁同筹,“湖南感化院开院宣言”,《感化》第1期(1928年),第59—61页。
<63>袁同筹,“湖南感化院布告”,《感化》第1期(1928年),第62—64页。
<64>龚云村,“创刊的话”,《感化》第1期(1928年),第2—9页;“总理遗嘱”,《感化》第1期(1928年),第1页。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6期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基督教”,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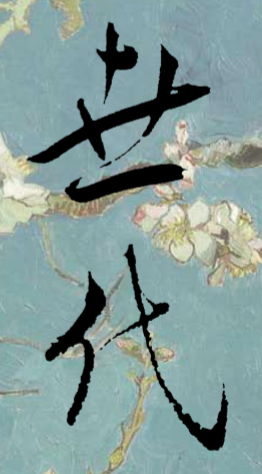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