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1224年或1225年生于意大利南部小镇罗卡塞卡(Roccasecca)。<1> 五岁时,他被送往本笃会(Benedictines)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 Abbey)学习,并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年时光。1239年,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下令疏散修道院,阿奎那转入新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在那里,他受到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又称作多明我会)吸引,于1244年接受托钵修会的会衣。然而,在前往博洛尼亚的途中,阿奎那被他的兄弟们绑架并软禁了一年。获释后,他前往巴黎继续学业,后成为科隆的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1200—1280)的助手。
1252年,托马斯开始在巴黎以学士身份执教,但很快卷入世俗教师与托钵修会教师的激烈冲突中。双方矛盾如此尖锐,以至于教皇不得不于1256年亲自下令巴黎大学授予托马斯授课许可,后又授予其神学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他撰写了《论真理》(De veritae)等重要著作,并完成了对波埃修(Boethius,480—524)的评注。1259至1265年间,阿奎那旅居意大利,在多所修院学校讲学。其间他继续撰写《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并完成了《金链注释集》(Catena aurea)。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萌生了创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构想。
1269年,托马斯重返巴黎开启第二次执教生涯,旋即再度陷入激烈论战。一方面,他捍卫道明会的神学思想,对抗奥古斯丁传统的保守神学家;另一方面,他抨击以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1240—1284)为代表的拉丁阿威罗伊学派——该学派于1270年遭到巴黎主教谴责。这一时期是阿奎那的创作高峰期:他完成或修订了大部分亚里士多德著作评注,《神学大全》的撰写也稳步推进。毋庸置疑,阿奎那最具原创性的神学贡献,正是在这第二次巴黎执教期间完成的。
1272年,托马斯离开巴黎前往那不勒斯,协助筹建多明我会总学府(studium generale)。他在此授课讲学、主持辩论,然而其著述活动却逐渐减少——直至1273年12月6日经历一场神秘体验后,他彻底停止了写作。不久,这位49岁的神学家在福萨诺瓦的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 of Fossanuova)病逝。<2>
阿奎那是公认的神学大师。<3> 然而,这位神学巨匠的属灵生命——尤其是他对基督徒身份的认识——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4> 事实上,如果脱离其“基督追随者”这一根本身份,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阿奎那的神学。因为他的生命与著作,无非是其基督教信仰层层展开的见证。与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1033—1109)等前辈神学家一样,阿奎那有着深刻的信仰根基。但不同于隐居修院的安瑟伦,作为大学里的学术型神学家兼托钵修士,阿奎那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折射出两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在承袭传统基督徒身份的同时,他以全新的方式活出这一身份——这是对13世纪新文化环境的创造性回应。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论证:面对13世纪欧洲的新变革,阿奎那选择以“道明会托钵修士”和“圣言教师”的双重身份践行他的基督徒使命。换言之,对阿奎那而言,作基督徒即意味着参与基督的贫穷与使命——而作为道明会士,他尤其注重通过宣讲圣言来实现这一身份。
然而在临近生命终点时,托马斯意识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使命已然完成——他正期待着一种更深刻的参与:与基督本体的合一。这种灵性进路恰与人类认识上帝的三重境界相呼应。<5> 阿奎那对基督的参与同样呈现出三重境界:青年时期作为“基督里的穷人”、中年时期作为“基督里的神学家”、暮年时期作为“渴慕与基督合一的密契者”。<6> 下文将首先简要分析13世纪社会变革与道明会兴起的关联,继而系统追溯阿奎那在基督里的三重身份演进:参与基督的贫穷、参与基督的教导使命,以及最终参与基督的生命本体。<7>
一、社会变革与多明我会的兴起
阿奎那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与思想变革,这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道明会。正如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所指出,如同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一场同样关键的改革”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头三个世纪里席卷了西方基督教世界。这场改革的重要特征,是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统一的现实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将统管整个世界。<8> 这种愿景使得教会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修道院的高墙之内,而是要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其管辖范围,从而使基督真正成为万有的主宰。这一理念对中世纪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针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十字军东征,正是对这一理想的回应。而道明会以上帝之言(而非刀剑)为武器使异端归正的精神,同样源于这种激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入神学体系,以及他构建《神学大全》的努力,都体现了这种“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的宏大愿景。<9>
11至12世纪的欧洲见证了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农业创新与领土扩张催生了经济繁荣,同时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镇发展,商业贸易与手工业行会迅速壮大。在此背景下,学者与学生组成的学术行会应运而生,最终演变为中世纪大学。这些大学被形容为“11、12世纪欧洲城镇结社浪潮的自然产物。”<10> 这场变革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稳定结构。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加剧贫富分化,物质繁荣滋长精神懈怠;城市人口激增导致传统教区体系难以满足牧养需求。<11>“当时社会深陷危机——异端思想导致分裂,物质欲望侵蚀信仰,权力贪婪败坏道德。在此背景下,那些为基督放弃世界又以基督重获世界的托钵修士,通过宣讲圣言提供了根本解决方案。”<12>
道明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13>多米尼克(Dominic,1170—1221)在参与法国南部阿尔比派(Albigensians)改宗运动时,敏锐地意识到:许多正统教士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已使其宣讲的福音失去说服力。这种洞见促使他确立“言行相济”的传道原则——上帝之言的宣讲必须与福音生活互为印证。正如传记作家所称,多米尼克堪称真正的“福音之人”(vir evangelicus)<14>, 以双重的革新践行福音:既宣讲圣言,又效法基督的贫穷。这一愿景最终孕育了新型的“宣道弟兄会”——他们以研习与活出上帝真道为毕生使命。
道明会虽在灵性上与隐修传统一脉相承,但作为应对社会新变革的产物,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追随基督之道——这种革新“彻底撼动了13世纪初的教会世界。”<15>这些托钵修士摒弃了秩序井然的修道院生活,向传统隐修制度发起挑战。当修道院在封建体系中享有经济和政治特权时,他们却毅然拒绝财富与权力,甘守清贫,只为在这个日益追逐物质的世界中为基督作见证。更引人注目的是,当传统修院坚守“稳定”的戒律时,这些托钵修士却放弃一切安定形式,以乞食为生、四处游走,将自身完全交托于上帝之手。正是这种流动性,使他们得以牧养那些漂泊的城市人群。因此,当古老修院仍盘踞乡野时,托钵修士们已活跃于新兴城市——特别是大学之中。正如特纳精辟总结的那样:
道明会士不事生产,隐修士则躬耕陇亩;道明会士乞食为生,隐修士则自给自足;
道明会士居无定所,街头巷尾皆可布道,隐修士则誓守一地,属固定团体;道明会士栖身城市,隐修士常驻乡野;道明会士活跃于大学,钻研学院学问,隐修士的学堂只在回廊之内。然最根本者,道明会士以口传道,隐修士若不咏唱,便常默默流泪祈祷。<16>
因此,当托马斯·阿奎那选择成为道明会修士时,他便毅然投身于这种新型修道生活。在13世纪欧洲的动荡浪潮中,他决心以特殊方式活出基督徒身份——通过践行基督的贫穷,通过宣讲上帝的圣言,将迷失的世界重新赢回基督怀抱。
二、参与基督的贫穷
阿奎那的一生唯有透过其作为道明会士、参与基督贫穷的身份方能被真正理解。从初入道明会的抉择到临终最后一息,托马斯始终践行福音式贫穷,以此追随他的主——那位为叫世人富足而甘愿贫穷的主,那位来拯救世界却被世界拒绝、连枕头之地都没有的主。
(1)成为道明会修士
以托马斯显赫的家世,他选择成为道明会修士的决定堪称惊世骇俗。其父兰多尔夫(Landolfo)伯爵作为罗卡塞卡城的封建领主,本指望幼子能出任本笃会修道院院长——须知“院长作为真正的封建领主,在宗教能为政权赋予神圣性的时代享有崇高威望。”<17> 这个家族为托马斯规划的人生轨迹,本期待他成为当地集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于一身的显要人物。然而当他们听闻托马斯竟要加入托钵修会——说白了就是当乞丐,这一美梦顿时岌岌可危。在托马斯这样体面的贵族家庭眼中,那些修士与流浪汉别无二致,不过是“自甘堕落的无赖团伙。”<18>为挽回这个“迷途”的儿子,家族竟派人将他绑架,软禁在家。
必须指出的是,“托马斯绝非那种急于摆脱父母管束的叛逆青年。”<19>恰恰相反,他极为重视家族忠诚,甚至主张人应当爱父母胜过其他一切,包括自己的配偶。<20>可以想象,他违抗家族意志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明知自己的选择会让至亲痛心疾首,他依然义无反顾。作这个决定前,托马斯想必经历过撕心裂肺的挣扎——孝敬父母的天职与追随基督的召唤将他生生撕裂。但道明会士的赤诚之火,早已在这颗年轻的心灵点燃熊熊烈焰,使他甘愿为基督舍弃一切,包括家族责任。当基督的诫命“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在耳畔响起时,他选择尊荣基督而非顺从双亲。后来他在《神学大全》中为此立场申辩:“顺从赐人生命的众灵之父(参《希伯来书》12:9),远胜过顺从赐人血肉的尘世父母。”<21>因为有时,血亲家族反而会成为人献身于上帝的阻碍。托马斯曾如此断言:“在信仰的疆域里,按肉身论亲属者,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仇敌。”<22>由此可见,托马斯绝非斯多葛式的禁欲者,相反,他怀有炽热的情感与赤诚——正是这份赤诚,催生了他为基督舍弃万有的决心。而弃世从主本质上正是参与基督的贫穷,就此而言,托马斯违抗家命的举动,与“阿西西的方济各当年如出一辙。”<23>他违逆家族意志、执意加入道明会的抉择,实则是内心决志的外在彰显——为要与基督的贫穷认同。
然而,托马斯的家族始终未能理解他这份植根于福音的深刻信念。他们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一时热血,便将儿子囚禁在城堡中,指望时光能消磨这份狂热。殊不知,托马斯早已活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所属的是宗教与社会经济秩序水乳交融的传统封建世界,而托马斯却置身于福音精神重生的新时代,无数人正响应呼召舍弃物质享受,以效法基督的贫穷。这位年轻的修士一旦决志追随基督,便展现出磐石般的坚定。软禁未能动摇他分毫,当家人派妓女前来诱惑他放弃圣召时,他竟手持火棍将其逐出,以烈火般的赤诚守护着自己的誓言。<24>在软禁托马斯逾年后,这个家族最终妥协——他们终于明白,儿子的抉择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以毕生为期的奉献:他要藉着贫穷生活与基督认同,正如那位为拯救世人舍弃万物甚至性命的救主。
(2)捍卫道明会
道明会士对贫穷的坚守,不仅令个人与家族震骇,更使整个体制深感不安。正因如此,巴黎大学内托钵修士的存在遭到了世俗教师们的激烈抵制。尤其是圣阿穆尔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Amour)在获得几位主教支持后,更是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攻讦。其核心指控之一,便是托钵修士的贫穷实践将危及社会秩序与私有财产。<25>面对这些指控,托马斯再次投身激烈论辩,竭力捍卫道明会身份的正当性。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他为道明会坚守福音贫穷所作的辩护——他力证这种贫穷生活,实为效法基督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在基督尘世生命中所行所受的一切中,祂神圣的十字架被立为我们必须效法的首要典范……而在祂所有的教导中,贫穷(全然的贫乏)确为第一要义——基督被剥夺了一切外在财物,甚至达到肉身赤露的地步……正是这种十字架上的赤露,那些选择自愿贫穷者尤其渴望追随,特别是那些弃绝一切收益之人……由此可见,贫穷之敌亦即基督十字架之敌。<26>
因此,对阿奎那而言,基督徒参与基督的贫穷至关重要。作基督的门徒意味着效法祂,而效法的首要功课便是与基督的贫穷认同——尤其是十字架上那极致的贫穷。耶稣曾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故此在阿奎那看来,基督徒最根本的初始行动,就是向世界和旧我而死,好与钉十字架的基督联合——这正是福音贫穷的核心所在。参与基督的贫穷,因而构成了托马斯基督教身份认同的内在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他为福音贫穷的辩护,本质上正是对自身基督徒身份的捍卫。
(3)阿奎那的沉默
事实上,托马斯对贫穷的坚守,在其生命末期的沉默中得到最深刻的彰显。正值著述巅峰之际,他在一次神秘体验后毅然封笔。虽无法确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重要的是——阿奎那竟任由其巨著《神学大全》未竟而止。这与他当年违逆家族加入修会的抉择如出一辙,必然是个痛苦的决定。“已完成八分之七的巨著,他何尝不想终卷?世间作家,谁能抗拒完稿的迫切?”<27>倾注了这么多光阴与心血的作品,以他平素的写作速度,本可数月即成——却就此搁笔,这需要何等巨大的情感力量与灵性勇气。
关于这一决定背后的动机,或许存在多种解读,但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那便是托马斯对福音贫穷的坚守。正如青年时期他舍弃一切追随上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连著述也一并放弃,为要彻底与贫穷的基督联合——用他自己的话说,“直至赤身之境”。丹尼斯·特纳(Denys Turner)这样阐释阿奎那的沉默:
托马斯生命中最后三个月的沉默,乃是对托钵贫穷精神的终极回应——在那个十二月天,他放下了作为道明会士唯一能合法拥有并称之为己物的行囊:他作为神学家的个人著作。因此,这项毕生巨著的有意未竟,正是托马斯以道明会神学家身份留下的终极沉默,是他对贫穷基督所能提出的、最终极之自我弃绝要求的响应。<28>
三、参与基督的使命
作为道明会士,阿奎那对贫穷的坚守,与他对宣播上帝圣言的使命密不可分。正如基督为拯救世人并使其富足而甘愿贫穷至死,托马斯过贫穷生活,正是为更有效地参与基督的救赎大工。对他及所有道明会士而言,参与这救赎职分,首要便是宣讲上帝的圣言。这一信念,诚如我们所见,正与道明会创会的初衷一脉相承——多米尼克虽以灵魂得救为首务,但目睹正统司铎的财富与腐败如何触怒异端者后,他坚称宣讲必须与贫穷生活相辅而行。<29>由此观之,“道明会士视贫穷为增强辩驳异端之力的论据。其首要使命在于宣讲、教导与研究,而贫穷不过是达致此目的之途径。”<30>尽管这对托马斯而言或许有一些言过其实,但其中确有真理的闪光:他参与基督的贫穷,正是支撑他参与基督救赎大工——即宣讲与教导上帝圣言——的根基。基督徒必须在基督的生与复活中,正如在祂的死中,与基督联合。要全然与基督联合,人不仅需要效法基督的贫穷,更要参与祂的核心使命——救赎世界。因此,托马斯将宣讲上帝圣言作为毕生呼召,正是他与救主基督联合的重要方式,正如他坚守贫穷之道乃是为与钉十字架的基督联合。这正是基督徒身份悖论性的两面:属基督的人“既从世界分别出来,却又临在于世。”在13世纪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托马斯与道明会同仁敏锐捕捉到福音复兴的浪潮——基督徒被呼召“分别”于世,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临在”于世。<31>因此,托马斯对贫穷与宣讲的双重坚守,实则是他参与基督福音奥秘的体现。
正因如此,阿奎那作为“神圣教义导师”与“圣言教师”的身份,是其基督徒身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教师效法基督,亦成为连接两界的桥梁。但这桥梁如雅各的天梯,必须同时扎根于天与地——并包含双向的流动。因此,教师首先必须恒切寻求、研习并默想真理,方能忠实地向世界传递真理。这正是为何阿奎那作为教师,首先永远是真理的勤勉学子。其次,教师必须将真理传递给民众,使他们获得属灵的富足并归向上帝。因此,托马斯不仅是一位默观者,更是笔耕不辍、讲学不息。正如托科的威廉所见证:“他的一生无非是祈祷、默观、授课、讲道、辩论、著述与口授——这便概括了托马斯的圣召真谛。”<32>
诚然,阿奎那的一生是默观与行动的交织。他寻求神圣智慧时静默沉思,将真理传递给世界时又奔走不息。<33>这种双向奔赴的圣召图景,可见于托马斯就任巴黎大学神学教授的就职讲道——这篇讲道实质上是其作为上帝圣言教师的宣言。他在默想《诗篇》104:13(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时写道:“同样,神圣之光先照亮硕士与博士们的理智,继而藉他们的职分将这光传递给学生的心灵。”在论述了上帝真理的崇高本质后,托马斯进而剖释教师的职责:
试观教师之尊贵,其如群山之象征:山岳巍峨——神圣教义的教师们亦如此竭力追寻属天之事;山岳辉耀——群峰最先沐朝阳之光,圣洁师者亦最先领受神圣启迪;山岳坚垒——犹如山脉护佑四方乡野,神圣教师亦守护信仰免于谬误。是故,一切神圣教义的教师皆当:因生命见证之卓越而“被高举”,因教导内容之炽热而光芒四射,因捍卫真理之刚毅而坚不可摧。此三者正对应其圣召之职:宣讲、授业与辩难。<34>
这第一种动向——“竭力追寻属天之事”——正是阿奎那智性生命的写照:他毕生致力于寻求与默观智慧,尤其是神圣真理。正如幼年时便提出“上帝是什么?”这一惊人诘问,托马斯穷尽一生探寻上帝之知。他如此沉醉于神圣真理,以至常常神游物外,恍若超离此世。正因如此,众人皆知他是位深邃的默观者。而他的默观总与祈祷及热切求问密不可分。托科的威廉曾记载道:
托马斯并非凭借天赋才智获得知识,而是通过圣灵的启示与灌注;因为他每次提笔著述前必先祈祷垂泪。每逢疑窦丛生,他便转向祷告。待泪水涤净心灵后重返案前,便已获得光照与训诲。<35>
然而这位深邃的抽象思想家,从未因追求天国智慧而疏离尘世责任。相反,作为教师,他殚精竭虑地将所悟真理传递他人,恰如圣经所言“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马可福音》4:28)。依循道明会“将默观所得分施他人”的教导,托马斯坚信“为他人燃灯,远比独自发光更为可贵。”<36>正因如此,托马斯不仅潜心默观,更致力于讲学与著述。虽英年早逝,其著作却浩如烟海——这全凭他笔耕不辍的惊人勤勉。正如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ron)所言:“公允地说,他堪称工作狂,鲜少休息或搁置手头工作……托马斯以近乎危险的严苛方式不断鞭策自己。”<37>鉴于他高度重视默观与抽象思考这一事实<38>,尤为可贵的是,阿奎那毕生倾注大量心血为普通读者撰述。其巨著《神学大全》专为初学者而作,便足见其用心——他在序言中写道:
上主教义的导师,不仅应教导资深信徒,更当启蒙初学者(正如使徒所言:“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哥林多前书》3:1-2])。为此,本书旨在以适宜初学者的方式,阐明基督教义之一切要理。<39>
因此,尽管阿奎那本可毕生致力于“向往天上之事”的上升之道,他却始终未忘教师天职,毅然投身将真理传向尘世的下降之路。事实上,这种双重运动的践行,正是他对基督双重本体的参与——上升运动参与基督的神性,下降运动参与基督的人性,藉此神圣真理得以降临尘世,引领世界归向上帝。
四、参与基督自己的生命
在13世纪社会文化剧变的洪流中,阿奎那选择以参与基督的贫穷与救赎使命来追随主。他毕生践行福音式贫穷,致力于圣言教导的使命,只为将世人引回基督。其生平始终交织着行动与默观。然而生命将尽时,一次神秘体验骤然打破了这种模式——他掷笔绝书,以圣言教导参与基督使命的活跃生涯就此终结。我们前面已论及,这一沉默实为托马斯在基督贫穷中的身份宣言。但其中必有更深意蕴:托马斯所经历的体验如此深邃,以致他坦言:“我笔下所写的一切,与我所见相较,不过稻草而已。”<40>对此,有人解读为托马斯对自身著述的全盘否定。然而更应看到,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其著作的价值,而在于他所见神秘异象的绝对超越。托马斯毕生致力于参与基督的贫穷与使命,但此刻,他濒临一种更直接、更亲密的参与——参与基督生命本身;与基督本身相比,万物皆黯然失色。因此,在其生命终点,阿奎那已预备好进入最高层次的参与——与基督本体的神秘相交(κοινωνία)。虽然这是托马斯基督徒身份认同的第三阶段——亦即全新阶段——但这种与基督的相交对他而言绝非陌生。事实上,这份对基督本身的渴慕——与基督终极合一——正是托马斯毕生的热忱,是其生命与事业的根基。据说,当基督赞许阿奎那“论我论得好”并询问他有何所求时,这位神秘主义者唯有一句回应:“Non nisi Te(唯你而已,我主)!”<41>
*本文最初以英文发表,见Yonghua Ge, “Aquinas: Participating in Christ’s Poverty, Mission and Life,” in Sources of the Christian Self: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ristian Identity, ed. James M. Houston and Jens Zimmerman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8), 328-40. 感谢Eerdmans出版社授权许可翻译。
<1>学界普遍认为阿奎那的生年当在1224年或1225年,然亦有部分文献提出1226年乃至1227年之说。Jean-Pierre Torrell,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 1, The Person and His Work, trans. Robert Royal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1.
<2>据首位为托马斯立传者记载,这位哲人于1274年3月7日清晨逝世,享年49岁。见Vita S. Thomae Aquinatis auctore Guillelmo de Tocco 65, 139.
<3>事实上,阿奎那亦被众多学者尊为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参见Norman Kretzmann and Eleonore Stump,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qu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
<4>现有一些著作探究阿奎那的灵修思想,例如Jean-Pierre Torrell,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 2, Spiritual Master, trans. Robert Royal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3) ; Robert Barron, Thomas Aquinas: Spiritual Master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这两部著作均深入剖析了阿奎那神学体系对其灵修思想的呈现与融贯。然而,学界对其作为神学家的生平著述如何反映其基督教身份认同,尚未给予充分关注。
<5> ST 1.93.4.
<6>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而恰似贯穿托马斯一生的三重主题变奏。不过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他或许会特别侧重于某一主题的彰显。
<7>本文将着重探讨前两个主题,对最后一个主题的讨论则从简处理。
<8> Diarmaid MacCulloch, Groundwork of Christian History (London: Epworth, 1987), 125.
<9>确实,基督在阿奎那神学体系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关于基督在其灵修神学中的角色,可参阅Jean-Pierre Torrell, Christ and Spirituality in St. Thomas Aquinas, trans. Bernhard Blankenhor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1), chap. 5.
<10>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 17-18.
<11> Justo L. Gonzá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1,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4), 302.
<12> William R. Cann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Middle Ages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60), 224.
<13>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修会亦于同期兴起。尽管这两个托钵修会都秉持福音式贫穷的信念,但道明会对宣讲上帝圣言热忱尤炽。
<14> John of Saxony, “Libellus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 in Monumenta Ordinis Praedicatorum Historica, ed. H. C. Scheeben (Roma: MOPH, 1935), 16:75.
<15> Denys Turner, Thomas Aquinas: A Portrai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16> Ibid., 17.
<17> Marie-Dominique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in Theology, trans. Paul Philibert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2002), 4.
<18> Turner, Thomas Aquinas, 12.
<19> Ibid., 13.
<20> ST 2-2.26.11.(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论述为:“爱的等级可以从善或者从与爱者的连系来衡量。从作为爱的对象之善那方面来看,应该爱父母胜于爱妻子,因为爱父母是将父母视作自己的根源,并认为他们是更高尚的善,而爱他们的。不过,从连系方面来看,就应该更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她与自己的丈夫结为一体,如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6节所说的:‘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因此,人更热切地爱妻子;可是,他应该更敬爱父母。”此处引文见《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二部·第26题,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2008年,第92—93页。引用时有改动。——编者注)
<21> ST 2-2.189.6.
<22> Contra Retrahentes 9, Leonine, vol. 41, p. C 57, quoted in Torrell, Person and Work, 17.
<23>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7.
<24> Bernard Gui, “The Life of St. Thomas Aquinas,” in The Life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Biographical Documen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nelm Foster (Baltimore, MD: Helicon, 1959), chap. 7.
<25>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10.
<26> Contra Retrahentes 15, Leonine, vol. 41, p. C 69, quoted in Torrell, Person and Work, 16.
<27> Turner, Thomas Aquinas, 44.
<28> Ibid., 45-46.
<29>教宗何诺留三世在给道明会的推荐信里明确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向你们推荐我们亲爱的孩子们——道明会的传教士们。他们通过立下贫穷誓愿、遵守会规生活,完全投身于传播上帝圣言的事业。”教宗还指出:“他们工作的预期成果和终极目标······就是灵魂的救赎。”Quoted in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12-13.
<30> González, Story of Christianity, 305.
<31>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11.
<32> Quoted in Martin Grabmann, The Interior Life of St. Thomas Aquinas, trans. Nicholas Ashenbrener (Milwaukee, IL: Bruce, 1951), 12.
<33>在阿奎那看来,默观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的关系,正如爱上帝与爱邻人之间的关系——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同一圣爱(caritas)的两个面向。正如他在《神学大全》中所言:“默观之德催生行动之力,而真诚的仁爱实践必引向更深的默观”(ST 2-2.182.1)。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体现了道成肉身的奥秘:永恒圣言既在静默中与父神交融,又在尘世中施行救赎行动。
<34> Thomas Aquinas, Inaugural Lecture (1256), quoted in Chenu, Aquinas and His Role, 60.
<35> Quoted in Grabmann, Interior Life of Aquinas, 12.
<36> Turner, Thomas Aquinas, 6.
<37> Barron, Thomas Aquinas, 23.
<38> ST 2-2.182.1.
<39> Preface to ST.
<40> Quoted in Torrell, Life and Work, 289.
<41> Quoted in Pope Benedict XVI, Holy Men and Women of the Middle Ages and Beyond (San Francisco: Ignatius, 2012), 70.
(作者为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神学研究院中文部主任)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5期的主题是“纪念托马斯·阿奎那诞辰800周年”,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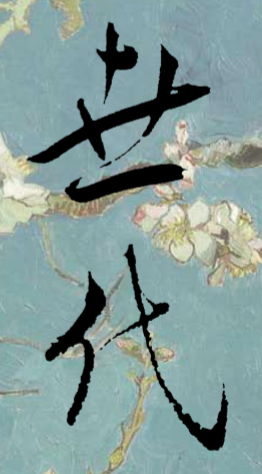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