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紧盯着满脸狐疑的仪瑞,像是在说,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打这房子的主意!”。绘图:曹青]
历史再长,总有起头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前后,天一路当时还叫辣蒙西罗路,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完工不久的新马路。它格局大气,环境清幽,沿路所盖的几幢西式小楼几乎都是还未完工便先有买家,唯独与皮柏底路交口的一幢,因为地形限制,只盖成普通的两层洋房,又因为紧邻俄侨的聚居地,完工后乏人问津。这一年,陈望涵自美国留学归来,打算在上海做棉纱交易,他急着要为妻儿找到落脚处,便不假思索买下它。
陈望涵的管家莫成稍能识文断字,十多岁便从乡下来上海讨生活。他原先在陈望涵的友人家作跟班,陈见他老实本分,说服朋友让他跟了自己。莫成的妻子阿瑶原在乡下伺候公婆,因为陈家需要保姆,也来到上海。陈家的人住在二楼,莫成夫妻俩住在一楼后厅旁的边间,相安无事,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陈家客厅的茶几上,总是摆放着一本有些卷了边角的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在客厅喝茶闲坐时,陈太太会饶有兴致地拿来细读,陈望涵每晚等待饭菜上桌前,也要翻开浏览几段。三餐前,主人夫妇必定会祷告谢恩,不仅为自己的一家求平安,也为莫成与阿瑶求。日子久了,阿瑶渐渐多了个心眼,上菜时总是先盖上碗盖,等主人说完那声“阿门”后再揭开。莫成则在一旁抱着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小少爷轻声劝哄,联想起主人对自己视如亲人般的恩待,他在心里觉得知足、感恩又羡慕。他乡下的家人拜菩萨,祭祖先,烧香叩头分外虔诚,也都是勤勉、辛劳的好人,但永远都活不出陈家人的欢喜与自在。
转眼到了三七年夏天,阿瑶已重孕在身,莫成原打算送她回乡下生产,连顶替的新保姆都物色好了。然而不出一个月,日军攻进上海,租界外成了沦陷区。莫成一筹莫展间,陈望涵夫妇提议让阿瑶在租界内的天主教医院生产,并承诺会垫付所有短缺费用,令莫成夫妻俩感激不尽。
又过不足一月,当中日两军战事方酣时,阿瑶要分娩了。这天一早,陈宅天井里一棵多年没有动静的桂花树突然结出一丛白色籽粒,凑近了闻,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为纷扰的时局送来一丝喜气。
阿瑶却因难产差点丢了性命。一大早,陈太太便赶去医院,守在产房外虔诚地为她祈祷,陈望涵也从办公室挂去电话,一再宽慰莫成。“主必保守”的祷告词言之凿凿,让莫成夫妇的心因此而安定不少。等到产房内终于传出婴儿响亮的啼鸣时,守了整夜的莫成感觉自己心底积郁的滞闷终于被哭声炸开一道裂缝,他第一次学着主人的样子,交叉双手举至胸前,虔诚默念着献上感恩。当晚,他恭谨地恳请陈望涵为孩子取名。陈思索一下后说,“弄璋之喜,全凭主赐平安,我看,就叫他仪璋吧,你觉得如何?”莫成自是喜出望外。
陈家少爷文泽刚满三岁,聪慧可爱,只是说话有一点大舌头。等到仪璋被抱回家里,他也学着大人用上海话叫他的名字,但听来听去,都好像是在叫“木桩”,惹得两家大人哄堂大笑。
战争把租界困成孤岛,又促成孤岛经济的变相繁荣。陈望涵的生意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于是让莫成跟着自己出入交易所,手把手地调教他生意上的事情。仪璋满周岁时,原先受战事波及的对外水路交通已恢复正常,莫成遂将妻儿送回乡下,自己专心在上海赚钱养家。
仪璋再回上海,是抗战胜利后的事情了。莫成用自己千辛万苦存下的钱在南市老城厢的沙角路上买下一套石库门旧房,终于能把妻儿接回上海团圆。阿瑶也不用再给人帮佣,平日还能穿着体面、略施粉黛,被邻居尊称一声“莫太太”。一年后,仪璋有了妹妹仪珍;再过两年多,家里又添了弟弟仪瑞。
陈望涵却总对时局有不安定的感觉,他把赚来的钱都存入香港的洋行里,预备不济时另作打算。一九四九年初,内战大局底定,陈望涵夫妇终于下定决心迁居香港。家中带得走的被分批运走,唯有房子,他们既带不走,也脱不了手。
除夕夜,陈望涵将莫成一家请到自己家中过年。两个男人把妇孺留在客厅,自己在书房中聊到半夜。十二岁的仪璋几次跑去听大人讲话,却并未被大人支走。陈望涵从上海的时局讲到自己的处境,最后从保险柜中取出陈宅的房契与一份拟好的声明,像是托孤般地交给莫成,不给对方任何推脱的可能。声明写在陈望涵常用的便笺上,页眉上方印一枚鲜红端正的十架图案。所有的重要条目都罗列得很周全,其中关键的两点是:房主暂离上海期间,房产的所有相关事宜由受托人全权负责;若房主在十年内无法返沪,则此房产完全归受托人所有。陈望涵的决定令莫成百感交集又无可奈何,十多年交往下来,两人虽一直有主仆之别,但更有兄弟般的默契与信任。他不再犹豫,很快在声明上摁下自己的指印。临离开时,莫成瞥见阿瑶的手中握着那本他熟悉的圣经。陈太太过来挽住丈夫的手臂,对莫成夫妇轻声说道,“谢谢你们如此重情守义,我们无以回报。这本圣经也留给你们,愿主赐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陈家三月离开,上海在五月宣告和平解放。军管会对上海各行业的接收有条不紊,莫成虽每日仍去棉纱交易所上班,但他非常清楚军事管制与体制重构间的必然性。多年来,他一直仿效主人,只把一部分现金存入银行,剩余的闲钱、银票和金条都被他锁进交易所的保险柜里。大局当前,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自己苦心积攒的家底,也曾想过送去乡下,但乡下正在闹土改,同样不太平。
一切远比莫成担心的来得更快。夏天还未结束,他就失业了,藏在交易所保险柜中的家当被全数充公。那天晚上,望着父亲满面愁容,仪璋觉得自己一下子便长大了。
街道给莫成安排的新工作是每天清晨打扫弄堂,他只能收起体面与自尊,重操初来上海时做过的苦力活。为了全家的生计,阿瑶除了不断变卖家中不多的值钱东西,还要每天背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替人洗衣做饭。区政府将他们在沙角路上的石库门房子隔成三套,一套给他们,其余的给两个南下干部家庭使用,发一些象征性的补贴。第二年,仪璋上初中,课余时跟人学做羽毛球卖钱。他把成袋清洗过的鸭毛带回家倒在天井的地上,一根根挑选修剪后插入底座,再用尼龙线与胶水定型。等做得熟练了,他又去揽别的活计,像是做女孩们踢的毽子。虽然所得微薄,毕竟让家中多了一点收入。几年间,莫家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总算相对平静。陈家托管的天一路私宅虽然也被暂时分给人住,但产权仍归莫家。
麻烦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随着政府对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陈宅也终究被人提及。那年夏天,仪璋考入同济的建筑系,征收陈宅的红头文件送来时,一家人仍在喜悦之中。莫成看完文件,精神恍惚地爬上阁楼翻找陈家的房契和声明。这些年来,他将它们夹在那本圣经中,藏在尽可能隐秘的角落里,毕竟,这些都是和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料,从阁楼上下来时,心事重重的莫成一脚踩空梯子,身体后仰着倒下去,头重重地砸在地板上,人当场就不行了。弥留之际,他指点着圣经与两份文件,咦咦哦哦地反复交待仪璋。仪璋扶着父亲的上半身,流着泪拼命点头,他明白,父亲无法守住的承诺已落在他的肩上。
莫家的丧事为仪璋争取到几日思考对策的时间,等到再也无法拖延时,他带着红头文件去天一路上的街道派出所。“我们觉悟不够,才答应帮资本家代管房子,但我们全家热烈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我建议政府把这房子当作反面教材,看旧社会资本家的洋房是如何被我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工厂!所以,我恳请政府暂时不要收回,我会把自己的代工搬进去,慢慢扩大生产规模,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说得有板有眼,倒真把那两个年轻干警给唬住了。盘桓几日后,事情出现转机,街道出面向区政府提出申请,将陈宅的一楼以低廉的费用租赁下来,改造成“跃进街道加工厂”,再安排十五名老弱残疾成为第一批工人。仪璋乘势再表态,愿意将陈宅无偿交给政府使用,唯独希望暂时维持产权现状,待陈家将来返沪时一并清算。
忙完这些事情后,大学早已开学。学校虽然仍旧同意他入学,但仪璋担心,一旦自己离开家,还会有难以预料的麻烦。在煎熬了三天后,仪璋办理了退学手续,也申请成为这家加工厂的工人。
几年间,仪璋不断扩大加工厂的规模,将陈宅的二楼改装成排字车间和印刷厂,又在一楼持续添置制作体育用品的器具。第二年,街道任命他作厂长,他虽然毫无兴趣,却仍应承下来,只为了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夜深人静时,仪璋偶尔也会想到自己早已错失的另一种人生可能,他觉得遗憾,但并不太难过。
仪璋在一九六四年夏天结了婚。当他还是个懵懂少年时,读过不少苏联的文学作品,也曾对爱情有过带着浓厚阶级色彩的向往。高中时,他与一个同班的女生有过短暂而纯洁的交往。俩人一起读《青年近卫军》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一起憧憬美好的将来。他考上同济时,女生进了复旦,俩人原本已打算将关系挑明,并向父母坦白。然而,自从仪璋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后,一切都化为泡影。女生原来并不打算离他而去,但他为对方着想,忍痛彻底断绝了关系,他的全部世界快速萎缩成眼前的狭小天地。玉秀是加工厂某职工的外甥女,家世清白,与父母同住在杨树浦的棚户区中。按说,这样的姑娘与仪璋原本是不相干的,但介绍人一再热心催促,仪璋也想到玉秀家的情形或许对自己有利,在充满未知的年代里,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更理想的选择。
也在这年夏天,仪珍高中毕业考入化工学院。与大学擦肩而过的仪璋似乎比妹妹更兴奋,请了假将她的行李驮到学校,还从少得可怜的结婚喜钱中分了一点给仪珍。又过两年,家里最小的仪瑞也从高中毕业了。文革的风暴无情裹挟了这个原本极其单纯的孩子,他居然公开声明,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充满了“封资修”的色彩,身为新时代的革命闯将,他要改名叫“莫一呼”,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声筒。
政治运动以铺天盖地的气势压来,全市仅存的私宅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令仪璋忧心忡忡。为求安全,他常耐着性子劝导员工,要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进门处的两面围墙被他糊满了标语,收音机也成天开着,语录歌播得整条街上都能听见。
没过多久,仪瑞果然带着红卫兵和房管所的人冲到加工厂,对他大声喝斥,“莫仪璋,你今天要老实交待!十几年来,你用各种手段独占反动资本家的私宅,拒不上缴政府,究竟是何居心?”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仪璋,仪璋一时没了主意,倒是房管所一个女干部关于南市旧房的诘问启发了他,那套莫成买下的私产早被瓜分了供三家人住,只因为莫家在分房上一再配合,才没有被收走产权。仪璋找到了回话的切入点,“我们一直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与其他革命家庭共同使用南市的房子,但的确没有向政府交出产权。这样吧,既然厂房在此,我们一家马上就搬来二楼侧边的那两间空屋住。南市的房子任由政府处理!”
仪瑞原想逼着大哥交出天一路上的陈宅,因为这里地段好,房子价值更高,若此事得成,他在红卫兵组织中无疑将更有地位。眼见如意算盘落空,不知所措的他当晚向仪璋大发雷霆,仪璋逼自己耐住性子不去理会他。但次日一早,他让玉秀替自己请了半天假,沿街找到一个施工队,央求了好久,终于说服两名建筑工把一部打桩车开到陈宅的门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陈宅正门的侧边打下一根木桩。他紧盯着满脸狐疑的仪瑞,像是在说,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打这房子的主意!
搬出南市旧房的那一天,仪璋几乎将所有心思都花在遮掩用绢布仔细包好的圣经上,生怕有任何闪失。几天后,仪瑞的人事关系被红卫兵组织退回街道,再也寻不到其他出路的他,只能接受下放的安排去了云南。
很快,仪珍要从化工学院毕业了。文革开始后,她的专业课几乎被完全荒废。学院前两届毕业生全都滞留校内参加政治学习,但到了仪珍毕业时,形势又变了,三届毕业生被同时分配工作。令仪珍大感意外的是,她被分配到闵行的一家农业技校教化学,虽然不在上海市区内,毕竟相隔不远。
区政府马主任的儿子与仪珍同校,是前一届的毕业生,可能在校时得罪过领导,被分到宁夏偏远小城一个和他的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岗位。马主任得知以后满心怨愤,第二天便跑来加工厂,不动声色地对仪璋说,“你应该清楚,自解放以后,政府一直通融你家。其实,你这洋房十年前就应该交公了。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区里给你们三天时间,赶快把厂房清出来。至于新厂房,等区里安排后,再通知你们。”话一说完,马主任拂袖而去,但走到一半,他又回头丢下一句,“听说你妹妹分配得很不错嘛,恭喜了!”
直到马主任离开很久,仪璋仍是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多年来和自己从无瓜葛的马主任,为什么会突然闹上这么一出?反而是玉秀想到,这可能跟马主任儿子的毕业分配有关,看起来,马主任是想要逼着莫家把仪珍和他儿子的分配去向换过来。当晚,仪璋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不亮便蹬着自行车去化工学院找仪珍。见到仪珍后,他还没说两句,仪珍就明白了他的心思,眼睛立刻红了起来,拼命忍住眼泪。兄妹俩在校园中来回地走,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是仪珍扭过脸来问,“阿哥,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帮陈家守他们的房子?我们到底欠了他们什么?”仪璋的眼睛也红了,他回答着仪珍,却像在对自己说话,“答应人家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总不能言而无信。阿爹在的时候,不是一直这样教我们的吗?”
陈宅的所有权再一次被莫家保全下来。几天后,仪珍悄悄地离开上海。临行前,她借故学校还有事情,没有再回天一路向任何人道别。
转眼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年底,市政府对本市遗留的私人住宅归属问题作了调查与批示,鉴于陈宅的具体情况,判定其所有权最终属于莫家。批文下来后没几天,阿瑶匆匆辞世。很快,“跃进加工厂”也在改革大潮中销声匿迹,仪璋夫妇把十来岁的儿子托给玉秀的父母照管,从头学做裁剪,努力另寻生活的出路。在知青返城大潮的裹挟下,仪瑞也回到了上海。无所事事的他有一贯精明的生意头脑,仪璋夫妇便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帮忙招呼生意,购买衣料。
一九八四年初秋,夫妻俩把原先摆在弄堂口的裁缝铺搬进新开的服装市场里。他们的儿子也从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无线电厂,全家的生活似乎终于迈上正轨。某天,街道送来了一封由侨办转交的国外来信,信中提供了陈宅在解放前的确切地址与房产的有关资料,还提到仪璋的父亲莫成的名字。寄信人希望侨办能帮忙找到莫成或他的家人,也想要了解陈宅的现况。
仪璋就这样与他早就印象模糊的陈家少爷文泽牵上了线。次年仲春,陈文泽与妻子来到上海,当出租车停靠在天一路上自己的旧宅门前时,他一眼便从一群等候者中认出了仪璋。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是百感交集。进到屋里,他们坐在饭桌前客套地寒暄,就像几十年前他们的父辈一样。陈文泽讲起父母当年如何辗转到香港,又如何在六十年代初移民到美国。中美建交后,父母一直想要重回上海看一看,然而,不等夙愿达成,两人便先后离世。直到弥留之际,他们还念叨着上海的这座老宅。时隔多年,陈文泽说起话来还是有一些大舌头,让仪璋想笑。有几个瞬间,仪璋也有重提往事的冲动,然而,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他想,这房子或许只是陈家人存储记忆的器皿,却成了他身上流淌血液的器官。
“我父亲一直说,一定要好好谢谢你们全家!”临离开前,陈文泽从手提箱里摸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递给仪璋,“这是一点点心意,是我父母生前一直交待要给你们的,谢谢你们全家人替我们守住了这幢房子。”仪璋接过信封,轻轻摩挲了一下点头致谢,“这房子始终是你们家的,我们只是帮忙看管。如果你有需要,我们马上奉还。”得悉陈文泽要来时,他就已经找出那本悉心保存的圣经,预备好要在对方开口索要时归还两份房产文件。
出门时,陈文泽注意到了门前那根突兀的木桩。在他的记忆中,旧宅门前原是开阔一片的,他想要开口询问木桩的来由,但跟在他身后的仪璋却抢先一步,替他打开了出租车的车门。
几天后,仪璋将信封里的五万美金悉数存寄给仍在宁夏的妹妹仪珍。多年来,她的日子一直过得清苦,想要调回上海的努力也屡屡落空。每次想到她,仪璋的心里都会隐隐作痛。
进入九十年代后,拆迁大潮终于一点点地席卷了天一路。按照规划,除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或名人故居外,天一路上的其余旧房将一律拆除。街道上门反复催促,政府的动迁方案也算优厚,除了经济补偿,还提供了位置与条件都不错的新建小区与优惠的购房价格。玉秀很兴奋,儿子正在谈对象,婚事已在考虑之中,分家势在必行。南市的石库门房子已经不可能再要回来,被当作二十年厂房的陈宅又已老旧不堪,儿子不愿意在这里过他今后的小日子。然而,说来说去,仪璋的回答却总是最简单的三个字“我不搬”。玉秀苦劝无果,只好自己在搬迁合同上签了字。
夏天之后,拆迁渐入高潮,沉闷的敲击声与房屋倒塌的轰响常在天一路上此起彼落,愈发孤立的陈宅像一颗钝拙又执拗的钉子,无奈地站在那里。看着强制拆除的告示终于贴上陈宅的前门,仪璋心里清楚,这一次,他再也无力与时局对抗了。他将那本藏了很多年的圣经找出来,小心翼翼地翻出里面与房产相关的字据与证件,放在床头柜上,看了又看。写着声明的便笺纸早已发黄、变脆、旧迹斑斑,唯有纸页顶端的十架图案依然鲜明、端正。
拆房的前一夜,玉秀和儿子被他打发去了岳父母的家里,母子俩明白他的心思,没再多说什么,只说次日一早便过来接他。
半夜里起了风,风刮得有些异乎寻常,像是要把孤零零的老宅吹倒。仪璋本来就睡得不踏实,这下子完全没了睡意,眼睛盯着窗外发呆。已经变形的窗棂终于还是被风扯开了插销,仪璋起身去关窗,又看见门前那根从来都不合时宜的木桩,仿佛他从小听说的十字架,聚集了悲苦,却又承载着承诺的力量。他转身,突然感觉胸口一紧,心跳如鼓点般密集起来。他摇晃一下,想扶着窗台慢慢坐下,脚却像踩在棉花上无法着地。他又晃了一下,后脑勺朝地板沉沉地砸下去。那本古旧的圣经也随之翻扣在地,苍青的封面隐现一个金色黯淡的“约”字。床头柜上那堆原先叠放整齐的文件被风扬起,飘来荡去,散落在仪璋的身体四周,仿佛撒了一地的纸钱,应和着一个逝去年代的哀鸣。
作者简介:方激,1998年4月受洗归主。医学物理计量师,现居美国新泽西州。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6期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基督教”,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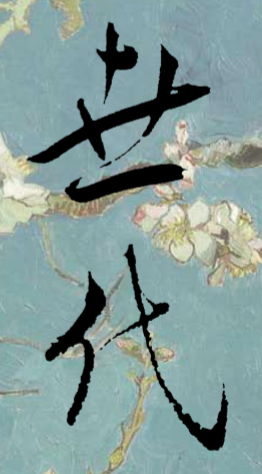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