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来源:amazon.com]
一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和活泼生命力逐渐为西方所知。因此,欧美新生代的学者也重新开始关注和探讨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并展现出与此前相关研究不尽相同的新貌。如果要在这一批学者中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那么就非美国学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1942–2019)莫属。他于2011年出版的《基督教在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一书,意义重大。<1> 一方面,该书可谓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耕耘这一研究领域三十年的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裴士丹在出版该书之后的次年秋天,从工作多年的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退休,所以该书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该书的中译本《新编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在2019年的年底出版, <2> 遗憾的是裴士丹在同年早些时候过世。
全书从唐朝到当代分为七章,按照时间断代展开。前两章分别讨论唐元两朝基督宗教(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和明清天主教,最后两章则分别讨论共和国初期与文革后的基督宗教。中间的第3—6章,亦即讨论晚清到民国的四章,被裴士丹称为全书的“核心”(第2页)。他对这核心的四章断代如下:第3章从19世纪初开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为止;第4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开始,到义和团运动结束为止;第5章从义和团运动结束开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止;第6章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二
该书标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新”字,读者自然会好奇:这一本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新书究竟“新”在何处?若将该书放在西方学术史的脉络中,书名中的“新”字最能够反映在作者对“本地视角”的足够重视及该视角背后的“跨文化过程”(cross-cultural process)范式之中。以往由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史,常常以外国传教士的角度,多使用西文史料,描绘出基督教单向输入中国的历史叙事。同时,在这一种历史叙事的范式中,主角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而不是本地信徒。
与这一种旧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是,裴士丹在每一章中都会花费不少笔墨,讨论那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他虽然不排除讲述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历史叙事中,他着力于探讨基督教与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跨文化过程”(第1页)。“跨文化过程”(cross-cultural process)这个概念,是裴士丹从爱丁堡大学的世界基督教史学者卫安德(Andrew Walls,1928—2021)在2001年编辑的题为《基督教史上的跨文化过程》(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一书中借用而来。裴士丹既然将基督教与中国相遇的故事描绘为“跨文化过程”,也就意味着不应该用基督教单向输入中国、中国被动接受的视角来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应该用更具动态的眼光来看历史上二者的相遇。一方面,传教士如何富有创意地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如何富有创意地接受基督教?
在这种强调“跨文化”的史观引导下,除了“跨文化过程”这个概念之外,书中也频频出现“跨文化”一词与其他词的组合,包括“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跨文化运动”(cross-cultural movement)、“东西方跨文化交流”(East-West cross-cultural exchange)、“跨文化学习经验”(cross-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 awareness)以及“富有创意的跨文化适应”(creativ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等(第2、11、18、19、94、197页)。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这本书的致敬人之一正是“阿伯丁的卫安德”。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明末清初、晚清和民国这三个时期之中选取个案,具体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的“跨文化过程”。
三
本书第二章的标题是“早期近代的耶稣会宣教及其命运”,仍然带有“宣教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痕迹。但是,裴士丹在其中用了不少篇幅讲述中国天主教群体的故事,反映了他对本地信徒作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接受者的重视。就我们所关心的议题而言,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裴士丹讨论明清天主教的“民间宗教化”现象时,反驳了以老一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为代表的学者对这段时期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的怀疑。从1580年代到1800年代早期,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天主教中心,包括北京、江南、福建、直隶和山东。在分区域描述这几个中心之前,裴士丹提到了城市天主教与农村天主教的分野。如果说耶稣会所主导的城市天主教吸引的主要是知识阶层的话,那么农村天主教社群的宗教意识则浸润在充满了神迹、异象与其他超自然现象的世界中。裴士丹认为,从宗教仪式的角度看,农村奉教者所经验到的天主教类似于传统农村的民间宗教(第25页)。这也正是裴士丹最早提出的“基督教的民间宗教化”或“民间基督教”(第33页)命题,该命题后来在连曦的著作《浴火得救》(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之中得到更全面的展开。<3> 根据这个命题,天主教带给农村信徒的“延续性”要多于“断裂性”。裴士丹指出,尤其到了18世纪后期,当天主教成为“非法宗教”,多数传教士不得不撤离,仅有少数偷偷躲藏在中国境内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宗教的实践与观念更慢慢地被本地信徒整合到宗教实践中(第25页)。裴士丹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来形容这种现象,并在注释中指出自己有意避免使用“混合主义”(syncretism)这一类可能带有负面意涵的词汇(第32、39页)。
在谢和耐著名的《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一书中,<4> 中国天主教适应中国传统的这种现象,却被诠释为这个时期的中国信徒的皈信并不真诚,因为他们皈信天主教主要是为了病得医治等好处,却并不真正在智性上理解天主教教理和圣礼的意义(第25页)。谢和耐认定那个时代的中国信徒不可能是真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无法被中国社会所真正理解。他的这一论断影响深远,笔者将之称为“谢和耐命题”。但是,裴士丹相信,如今并没有很多学者仍然同意谢和耐的这个一般性命题。裴士丹指出,如果以智性上是否理解信仰作为一个人是否可以算是基督徒的标准,那么在世界基督教历史上,也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理解诸如洗礼的神学意义、正统的三位一体观念等等(第25页)。谢和耐命题的症结,出在他以智性理解作为判定基督教的核心标准,这反映了他以类似“本质主义”的心态来理解基督教。裴士丹在征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家兰乐诗(Lars P. Laamann)的著作《帝制中国晚期的基督教异端》(Christian Here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ristian Inculturation and State Control, 1720–1850)<5>时,特别在一个注释中作出评论,指谢和耐在1980年代认为反映中国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缺乏足够理解、因此他们的信仰真诚度被加以怀疑的现象,在兰乐诗看来其实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文化融入”过程而已(第40页)。
不仅如此,裴士丹更质疑“谢和耐命题”背后反映出来的二元论的错误假设。实际上,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天主教传教士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产物,他们也无法脱离对神迹等超自然事物的感受(第25—26页)。换言之,即便在欧洲天主教内部,也可以找到天主教在中国的那些类似民间宗教的实践与观念。裴士丹并没有将这个论证扩展开来。类似的论证,后来在诸如汉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传教士的咒诅》(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中得到详细且有说服力的发展。<6>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过程”这一个在世界基督教研究领域发展出来的范式,如何在具体个案中挑战以往学界对“何为基督教”的本质主义观念,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基督教多样性的尊重。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新的研究范式对于裴士丹的影响。前文提到,裴士丹发展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基督教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呈现出“民间宗教化”的趋势。实际上,这个“民间天主教”的命题也反映在雍正朝禁教之后的政教关系领域。也就是说,从1724年到1840年代之间约一百二十年的禁教时间里,天主教越发融入地方社会;但同时,天主教社群也如本土的某些民间宗教团体一样,容易引起清朝官府的怀疑、监控与逼迫。清朝官府在全国范围内对某些民间宗教的逼迫,在1740年代后期、1784—1785年、1805年以及1813年之后都发生过,而天主教也得到了相似待遇(第33页)。
本书举四川天主教为例,具体说明天主教徒人数增长与清朝官府逼迫之间的张力。18世纪后半叶,四川天主教经历了大增长。到1800年之前,奉教人数可能达到了四万。裴士丹认为,在西方传教士缺席的情况下,四川天主教能够增长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18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中国神父的出现。裴士丹特别提到一个著名神父:清中期主要在四川事奉的陕西籍神父李安德(第34页)。他留下了长达七百页的拉丁文日记,该日记于1906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陆南(Adrien Launay)神父整理出版。裴士丹的著作虽然没有具体引用《李安德日记》,但对李安德的提及,反映出了裴士丹对于本地神职人员的故事的重视。
在此顺便指出这份日记的重要性。例如,1740年代后半期,李安德神父仔细调查了包括成都金堂、重庆涪州和叙州宜宾在内的教区里与教难有关的信徒。这份日记对教难的记载,俨然呈现出一幅中国版《沉默》的图画:其中可以看到“背教书”这类中国式“踏绘”,还有弃教的中国天主教徒(如赵若瑟)、中国神父(如苏神甫),也可以看到不顾逼迫、坚持信仰的中国式“认信者”(confessor,如传道员孙若瑟老人)。<7>
四
裴士丹探讨明清天主教的“跨文化过程”、重视本土信徒的思路,也延续到晚清新教来华的历史书写之中。
首先讨论1800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三章。在这一章中,重视“基督教民间宗教化”现象的裴士丹提出,这六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第61页)。由广东客家人洪秀全发起的这一运动,被裴士丹称为“中国第一个本土基督教运动”(第53页)。对太平天国的这一定性包含了“基督教”与“本土”两个元素。一方面,尽管学者们争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否属于基督教,<8> 但裴士丹认为至少该运动正式的信条——例如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太平天国版本的十诫——可以视为基督教的产物。另一方面,从太平天国领袖的行为表现上看,裴士丹又认为太平天国与中国民间宗教有更多的亲缘性(第54页)。
除了太平天国的相关人物之外,裴士丹在第三章中也用一小节交代了中国第一批本土新教徒的角色。他们包括中国头两名被按立的牧师梁发(1789—1855)和何进善(1817—1871),以及两位平信徒:一位是中国留学生先驱、幼童留美计划的发起人容闳(1828—1912);另一位是王韬(1828—1897),他对委办译本圣经的翻译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中国经典翻译贡献卓著(第61—62页)。对本土新教徒的重视,也反映“跨文化过程”概念在晚清新教历史中的应用。
到了第四章讨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结束的历史时,裴士丹依然专门用了一整节叙述中国基督徒的故事。在1860年的时候,中国新教徒只有几百人,但是四十年之后,已经增长到约一万人。裴士丹特别指出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及社会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若干城市基督徒群体在19世纪后期也渐露雏形(第78页)。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社群,出现在福州这一个《南京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裴士丹征引唐日安(Ryan Dunch)开拓性的专著《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分析基督教对于中国人在两种意义上的“属灵吸引力”。<9> 第一种属灵吸引力在于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差别。例如,对于福州美以美会的著名教会领袖黄乃裳(1849—1924)而言,基督教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解答了中国宗教没有处理的问题,并且能够帮助黄乃裳过上更有道德的生活。与第一种不同,第二种属灵吸引力在于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类同。亦即,对于另一些福州基督徒而言,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于它和中国民间宗教相似的超自然部分(神迹医病与异象等)。这些人愿意皈依基督教,或许不在于基督教提供了过道德生活的能力,而在于它比中国宗教的所谓“假神”更“灵”(第79页)。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本书对本土信徒的关注,以及贯穿全书的“民间基督教”命题的例证。
除了黄乃裳以外,裴士丹也扼要地叙述了另外一些中国基督徒领袖和精英的故事。他们包括协助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颜永京(1838—1898),以及与内地会合作的山西名牧席胜魔(1837—1896)(第81页)。裴士丹也介绍了石美玉(1873—1954)与康成(1873—1931)这两位江西美以美会的女基督徒,她们属于中国最早几名留学海外的女性(第80页)。
五
第五章讨论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基督教在中国进入二十年左右的“黄金时期”,不仅信徒人数两度倍增,而且本土教会领袖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此,裴士丹提出了为人熟知的“中西新教合作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概念;这个概念所涵盖的现象,或许最适切地表达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跨文化过程”。如果说新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可以看作从“西方差会时期”转为“本地教会时期”,那么“中西新教合作建制”正反映了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现象:日渐兴起的中国基督徒领袖渐渐被整合到原本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的现存“建制”之中,这样的建制既包括教会,也包括学校、医院、出版和青年会等基督教机构(第100页)。
裴士丹指出,这一种“整合”要到1910年之后才开始发生,并且最初只限于一小部分中国基督徒精英。除了义和团运动带来基督教需要本土化的刺激之外,“中西新教合作建制”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10年召开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第102页)。伦敦传道会年轻的诚静怡(1881—1939)牧师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崭露头角,并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成为“中西新教合作建制”最出色的一位代表(第101—102页)。具体反映“中西新教合作建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也都与诚静怡密不可分,其中包括1913年成立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和1922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后者被裴士丹称之为“中西新教合作建制”的堡垒之一(第102页)。<10>
“中西新教合作建制”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除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外,还可举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大学为例。就基督教青年会而言,加入该建制的中国基督徒领袖,包括第一任华籍总干事王正廷(1882—1961)和接任的余日章(1882—1936),后者任此职位长达近二十年。就基督教大学而言,例如最著名的燕京大学,吸纳了几位著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作为基督教教育学家、音乐家和心理学家的刘廷芳(1891—1947);中国最著名的神学家赵紫宸(1888—1979);中国史学家洪业(1893—1980),以及前清翰林吴雷川(1870—1944)(第102—103页)。
接下来,全书核心四章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六章)对“本土视角”和“跨文化过程”的最佳反映,就是裴士丹所称的“中国独立基督教”(Independent Chinese Christianity)的兴起。此处所谓的“中国独立基督教”,一方面包括了发展成为本土教派的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与聚会处,另一方面包括了个别的布道家。
根据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的关系为标准,笔者将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自立运动分为“藕断丝连型”、“中外合资型”和“自创教派型”。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可以作为“藕断丝连型”的代表,中华基督教会可以作为“中外合资型”的代表(属前文所述“中西新教合作建制”的一部分),那么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与聚会处等则可以作为“自创教派型”的代表。这三个教派的创始人尽管在他们信仰的早期都属于不同的差会教会,如魏保罗(1877—1919)原属伦敦会,敬奠灜(1890—1957)和倪柝声(1903—1972)原属美以美会;但是三人都相继从差会教会中独立出来,分别自创新兴的本土教派。我们无法对这三个案例展开详细叙述,但与本文旨趣关系密切的一点,就是裴士丹指出三个教派都持有一种前千禧年终末论的信念(第130、132、133页)。<11> 延续他早年关于耶稣家庭的研究,裴士丹特别对比了山东的耶稣家庭与三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的相似性。耶稣家庭的成员关于“被提”的见证,令裴士丹联想到义和团拳民施行“降神附体”的仪式实践。在他看来,二者有着共同的华北平原民间文化的起源。不仅如此,他认为耶稣家庭所持守的千禧年主义、末世很快来临的思想,与山东民间文化也有着相似性(第132页)。“民间基督教”的命题在此再次得以反映。
裴士丹所称的“中国独立基督教”,除了以上三个本土教派之外,还包括一些中国布道家。20世纪前二十年兴起的第一代中国布道家,有浙江的余慈度(1873—1933)(美国长老会和美国监理会背景)、江苏的李叔青(1875—1908)(美国监理会、美国圣公会和美国宣道会背景)和山东的丁立美(1871—1936)(美国长老会背景)。三人影响了不少后来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不过,中国本土的布道运动更重要的发展,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1930年代以来。这个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二代中国布道家,包括了192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巡回布道的王明道(1900—1991)(第136页),以及1930年代中期中国奋兴运动最为重要的人物宋尚节(1901—1944)(第137–138页)。这些中国本土布道家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西方学者撰写的通史中,再次表明“本土视角”与“跨文化过程”成为裴士丹书写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六
裴士丹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提到,全书关注的是所谓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因而几乎没有提到少数民族基督教和海外华人基督教(第1页)。这样的处理,反映裴士丹对“何为中国”这个问题作出比较狭义的理解。笔者认为,若我们扩展对“何为中国”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将少数民族基督教和海外/离散华人基督教纳入视野范围,绝不仅仅是将来书写基督教在中国的通史时必须补充的部分,也将体现新的历史编纂学再一次深刻的范式转移。
但无论如何,裴士丹完成了他那一代西方史家的任务。裴士丹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作为“跨文化过程”来理解;根据这个范式,他不仅如以往的学者那样仅仅讨论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宣教史”,也强调“本土视角”,尽可能地讲述中国基督徒的故事。在西方学术史的脉络下,裴士丹的著作不愧于书名中的“新”字。我们也可以借用宋代词人苏轼(1037—1101)的名句,来形容这本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1>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下文以文中夹注引用该书。
<2>裴士丹,《新编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尹文涓译,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9年。
<3> 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Lars Peter Laamann, Christian Here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ristian Inculturation and State Control, 1720–1850 (London: Routledge, 2006).
<6>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7>李安德,“《李安德日记》节译”,李华川译,《清史论丛》2013年号,第355—356、359、362、364页。关于李安德的中文译稿,亦参见“《李安德日记》节译之二”(《清史论丛》2015年第1辑);“《李安德日记》节译之三”(《清史论丛》2016年第2辑);“《李安德日记》节译之四”(《清史论丛》2017年第1辑);“《李安德日记》节译之五”(《清史论丛》2018年第2期);“李安德神父日记摘译”,张西平、张朝意主编:《国际汉学译丛》(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3年。该日记的原文可参见André Ly, Journal d’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Texte Latin. Introd. par Adrien Launay (Paris: Alphonse Picard, 1906), accessed June 12, 2023,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039570?rk=21459;2#.
<8>最新关于太平天国神学的著作,参见Carl S. Kilcourse, Taiping Theology: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843–6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关于作为“中西新教合作建制”之堡垒的协进会如何瓦解的历史,参见宋军,《变局中的抉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历史的终结(1949—1951)》,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7年。
<11>笔者亦曾在一篇关于连曦《浴火得救》的书评中指出,前千禧年终末论是连接该书所有研究对象的元素。参见王志希,“谁的“救赎”?哪种“民间”?——读连曦著《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5年第42期,第273—294页。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名誉副研究员,目前正在攻读加拿大艾尔伯塔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华人基督教史、加拿大基督教史和数字人文。)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2期的主题是“文化本位主义”,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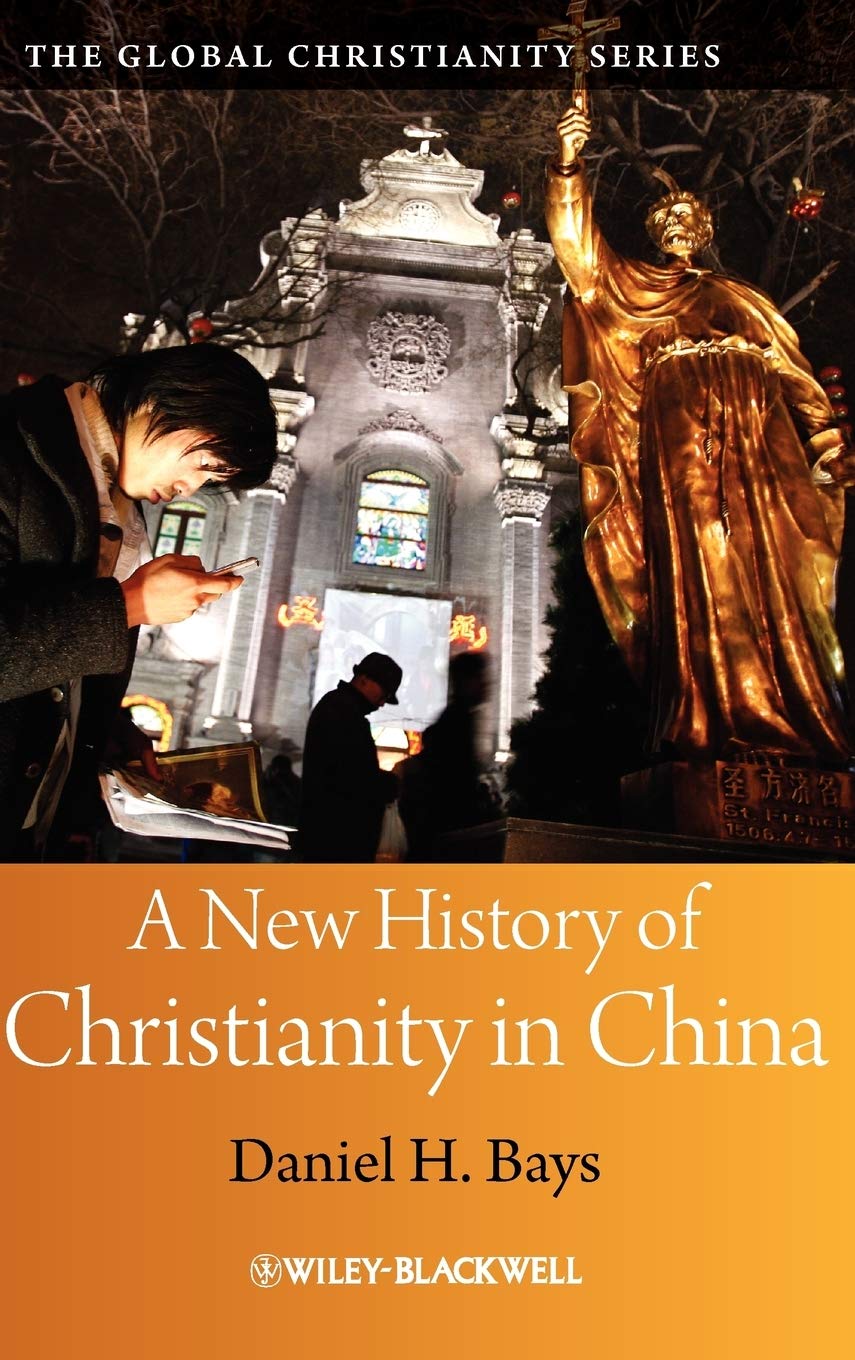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