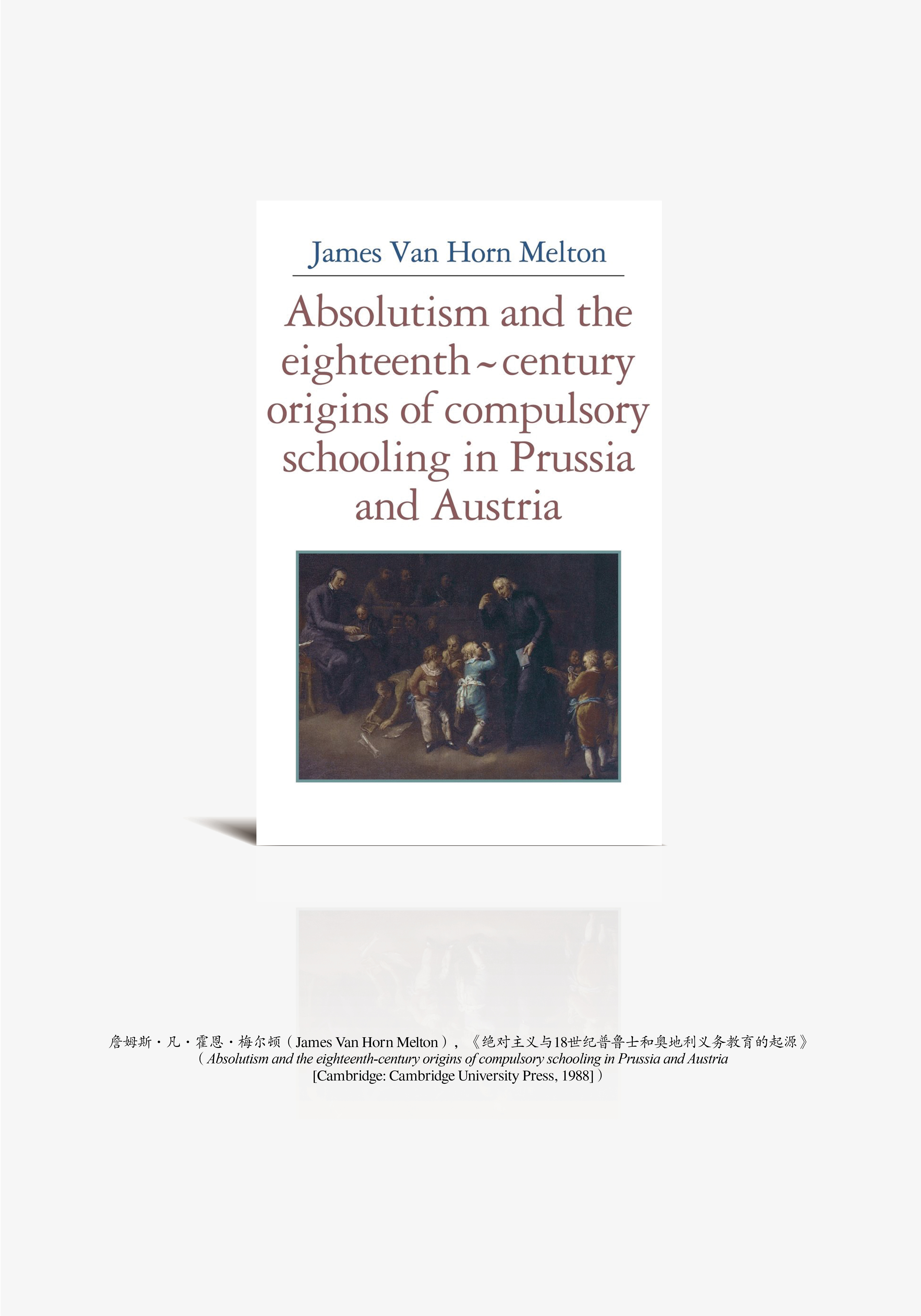
[题图:詹姆斯·梅尔顿,《绝对主义与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义务教育的起源》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0年秋冬合刊号总第12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本期杂志刊登的有关改教家论基督教教育的两篇文章(《菲利普·梅兰希顿论归正教育》、《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犹如一扇窗口,借此我们得以稍览16世纪主要改教家的基督教教育观。尽管梅兰希顿和加尔文在预定论和拣选等教义方面存在分歧,但二人在主张回到圣经、培育有学识的敬虔(learned piety)以重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进而实现教会的改革等方面,则是同道中人。<1>
像马丁·路德一样,梅兰希顿和加尔文均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也都认为教育对于改教运动取得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不仅是考虑到因新教与天主教分裂后原先的教育体系受到冲击,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更为内在的原因是,由于宗教改革强调阅读圣经对信仰重建的重要性,提高民众识字率、实现教育普及自然是改教运动的应有之义。诚然,改教家在引入自由技艺或者古典教育、建立分级制教学、使用教理问答、创办学校等方面复兴了基督教教育,推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但宗教改革在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其实主要还是在普及教育或者大众教育层面。从16世纪开始,改教家们就已有意识地系统地致力于开展教育事工,使得教育的范围不只包括传统的精英子弟,还包括普通阶层的子女,<2> 其结果是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于社会各阶层的学校,实现了教育权力由教会、社会到国家的转移。<3>
事实上,改教家本身就参与到实现这一教育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在16世纪所谓的基督教政体(Christian polity)中,政治权力和教会治理紧密相连。早在路德的时代,改教家就认为教育在塑造宗教信仰和市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灵性更新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们与政府当局紧密合作,起草学校章程,拟定教育政策,在整个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共颁布了超过100项学校条例。<4> 路德极为关心儿童在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甚至主张地方官强制民众送其子女上学,确保教会领袖和世俗政府不至于因为缺少合格的人选而衰败。这可以说是改教家提倡义务教育的先声。
一般而言,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被认为是19世纪现代工业社会的创造,通常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播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中欧新教和天主教的教职人员、贵族、市政官员就已规定宗教教育对其臣民而言是义务性的,国家开始负责儿童的教育问题,父母则要为此承担费用。但这一阶段的许多教育措施是临时性的和试验性的,教育史上由国家主导的现代义务教育之真正出现,要追溯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于1763年和1765年颁布的教育法令。有意思的是,18世纪义务教育之最终形成,同样与另一场“宗教改革”,即17世纪后期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密不可分。美国埃默里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凡·霍恩·梅尔顿(James Van Horn Melton)的著作《绝对主义与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义务教育的起源》,就揭示了成为义务的教育,如何在敬虔主义教育家的改革下,服务于18世纪兴起于中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治理,最终参与到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5>
本书除了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义务教育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起源,显明敬虔主义如何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培育民众内在的虔诚和服从。
第二部分从教育改革的文化和宗教根源,转向社会和经济背景,特别是关注普鲁士和奥地利乡村地区生产关系的转变,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道德自主性。而敬虔主义的教育,因其强调内在纪律和服从,提供了促进这一自主性的有力工具。第三部分集中考察腓特烈大帝1763年和1765年的学校法令,以及奥地利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女王1774年学校法令的实施情况。全书旨趣虽不在论述敬虔主义的教育遗产,而是说明教育如何成为绝对主义国家实施社会规训(social discipline)的手段,但该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敬虔主义对义务教育之影响,再次让人看到继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与世俗政权的互动,对西方教育乃至今天的现代教育之深远影响。这些影响有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比如作者提到,在今天的公立学校中,比起16世纪的改教家,他们的属灵后裔——17世纪后期兴起的敬虔主义,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教育印记。例如今天公立学校的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儿童使用的教科书,要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批准,而17世纪敬虔主义的学校最先要求小学教师接受正式培训,进而产生了最初的师范学校。敬虔主义的改革者们,率先致力于小学教科书的标准化。小学生在课堂上有问题时要先举手,这是敬虔主义的一项发明。大多数学生在一起接受教育,而非个别辅导,这在1740年代以前的德国小学教育中并不常见,而在此之后敬虔主义改革者普及了这一做法。(xiv)
敬虔主义最初是对17世纪日益走向僵化和学院派的路德宗的反抗,强调更为内在的、情感热烈的同时也是更为实际的基督教,尤其认为生活圣洁、注重行动,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标志。故此,他们强调祷告、社会福利和慈惠事工,在全世界积极开展宣教。此外,敬虔主义特别强调人人皆祭司这一教义,认为教会的复兴要通过教牧阶层和平信徒阶层之间的积极合作,因而鼓励平信徒读经和学习。<6> 这些信仰特征在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注重建立慈善学校和其他各类教育机构,特别强调提高普通大众的识字率和教育普及。敬虔主义的重要代表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就认为,教育是解决穷人道德败坏唯一有效的办法。故此,他于1695年在普鲁士小镇哈雷(Halle)附近建立了一系列学校,最初招收乞儿和孤儿。学校以敬虔和纪律严格闻名遐迩,后来逐渐吸引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送其子女入学,并发展为多种类型的教育机构,包括为进大学和从事官僚职业做预备的寄宿学校、为中产阶级家庭孩子提供教育的职业学校、孤儿收容所、针对穷人子弟开办的小学和培训教师的学校。(第57页)一时间,哈雷成为普鲁士敬虔主义的教育中心。这些教育方面的努力实际上继承了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的教育理念,即相信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所有人都应接受教育,以预备服侍上帝,服务世俗掌权者和整个社会。
与敬虔主义之父施本尔(Phillip Jacob Spener,1635—1705)一样,弗兰克相信内在敬虔的培育,需要对基督及其教训的真知识,这唯有通过阅读圣经才能获得。他们比路德更加强调平信徒读经的重要性,使得敬虔主义几乎被看作是(圣经)话语的宗教(a religion of the word)。(第39页)提高民众的识字率自然也成为敬虔主义的教育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正是通过与当权者合作。腓特烈一世积极资助敬虔主义学校的建立,甚至向东普鲁士地区的学校分发了数以千计的圣经,好让其臣民知道上帝的话语。(第48页)另一方面,敬虔主义的教育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对权威的顺服。这种顺服不是出于害怕受罚,而是源于内心因着信仰的缘故甘愿服从。弗兰克就认为仅仅是外在的顺服,就像外在的敬虔那样是不够的。这种对待权威的态度,自然与18世纪主张绝对主义的政治改革派产生共鸣。后者相信,国家如果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不能像以往那样直接采取强制力量,而应该以较为软化的方式比如从道德和教育入手,实现权威在臣民心中的内在化。这样,敬虔主义的教育就为绝对主义国家提供了控制社会的潜在工具。(第57—58页)
当然,这不是说绝对主义的国家统治不再需要法律、军队等强制力量,而是说学校教育特别是敬虔主义的宗教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统治的潜在工具,越来越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宗教改革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教育中的宗教目标和公民目标有严重冲突,他们甚至依靠政权力量来推动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政教关系往往呈现出相互利用又彼此牵制的特点,这或许是欧洲绝对主义国家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原因,<7> 也是当我们提说近代以来教育普遍成为一项国家事业时应有的区分。当基督教教育成为一种义务,往往指的是外部政治权力对教育的介入,教育的目标、政策、管理也就逐渐受制于世俗政权的需要,进而预示了教育后来成为实现统治的某种工具,而不再坚持以培育完全、真正的人为其目标。这是改教家和敬虔主义改革者与政权联合办教育要付出的代价,但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乃至基督教教育对社会公共领域发挥影响,若缺少当时当权者的支持与推动(无论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还是某种形式的宗教热忱),无疑难以取得实际进展。总之,在重新回顾宗教改革乃至敬虔主义的基督教教育遗产时,梳理政教关系或者教会、国家与教育的互动,既关乎对宗教改革教育遗产的全面理解,也是反思当前基督教教育生存处境的重要参照。
<1> Randall C. Zachma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the shape of his writings and though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16-29.
<2> 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3>博伊德 金 合著,《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训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4> Gerald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8,13.
<5> James Van Horn Melton,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Koppel Shub Pinson, Pietism as a factor in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8), 14.
<7>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2期(2020年秋冬合刊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2期的主题是“基督教教育”,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