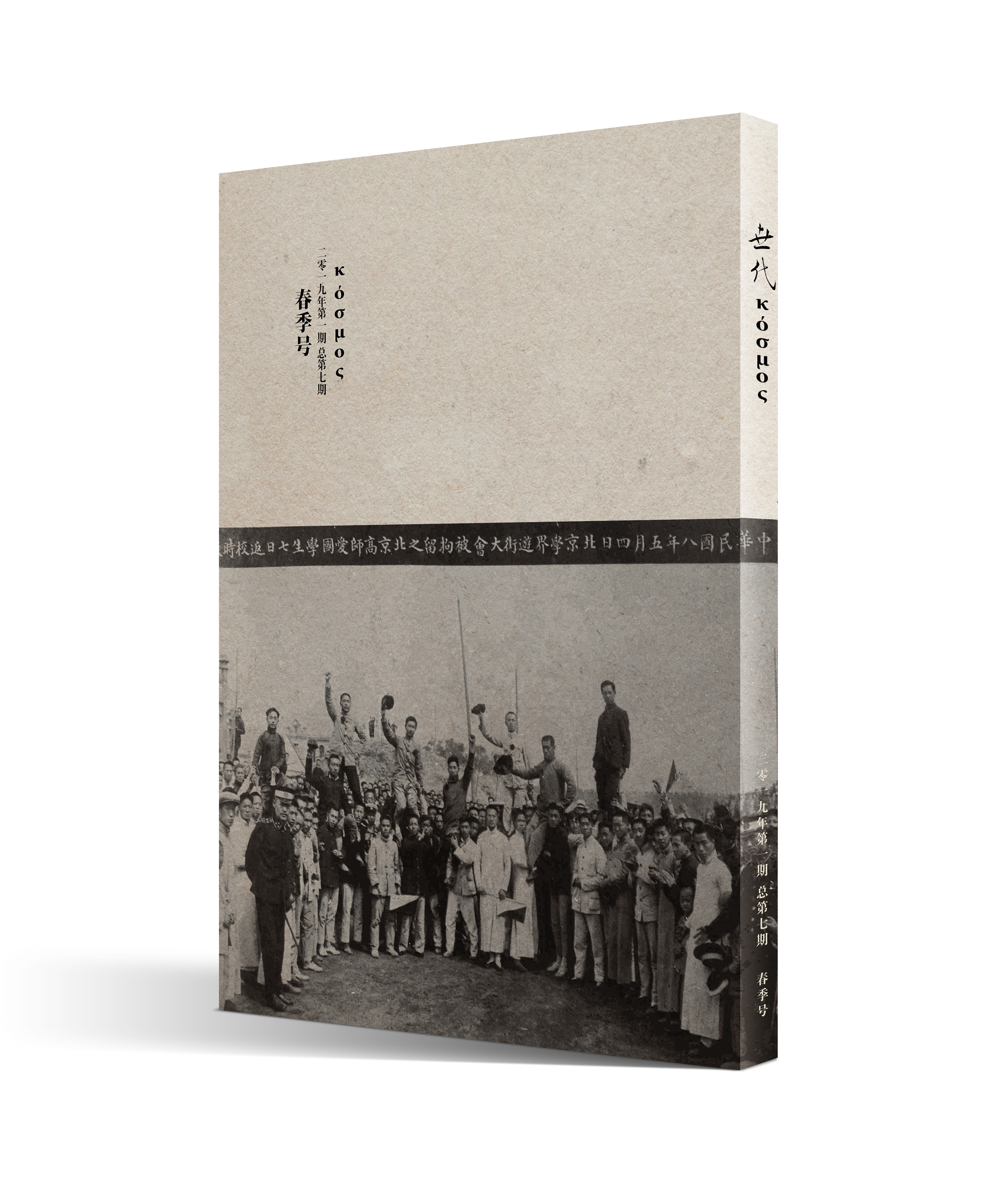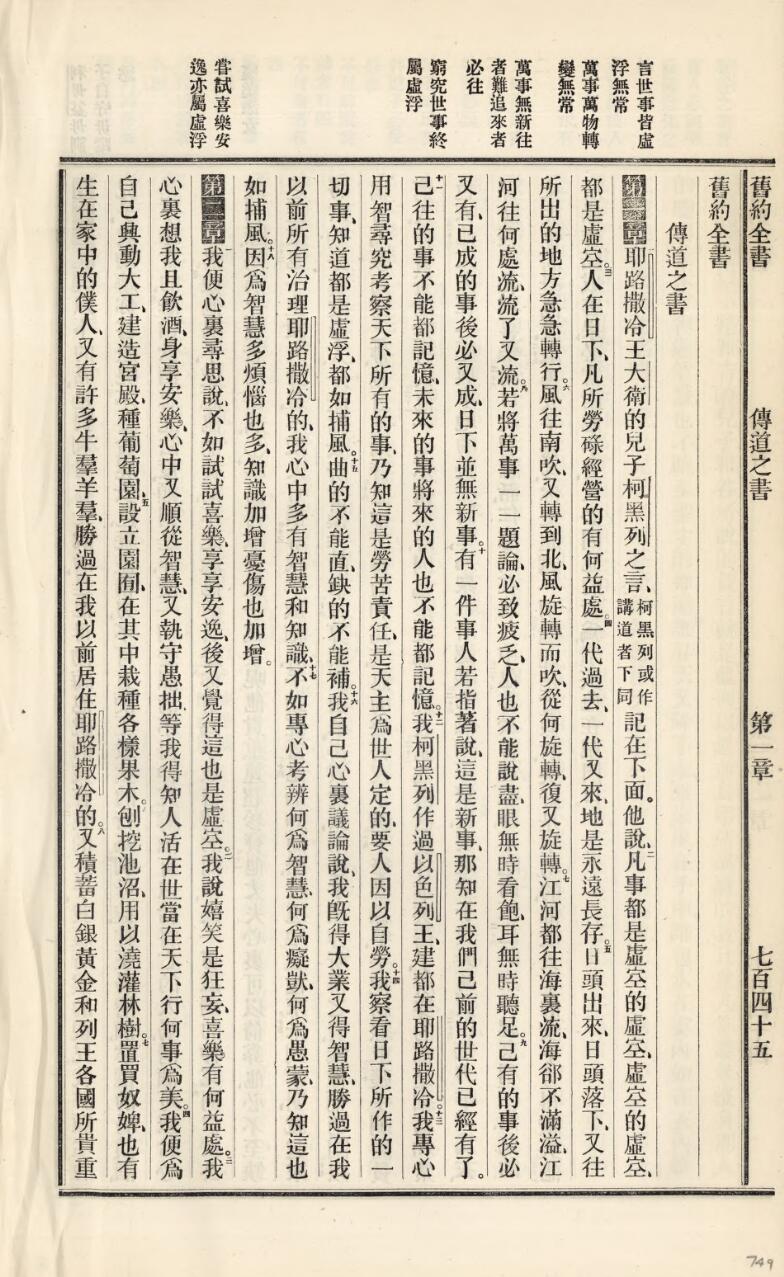
2012年底,我有幸受邀参与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新汉语译本”圣经旧约部分经卷的润饰与审阅工作。此前不久,“新汉语译本”圣经新约历时16年的翻译和审校后出版。
这套新译本的翻译目标是力求忠于原文的信息、表达方式与感情色彩,又贴近生活,用语明白晓畅。<1> 其翻译原则尤为强调忠实性,特别体现于译文在符合汉语语法并传递无歧义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脉络标记和词序安排,如重复的字词、同源词的布置、功能词的运用,以及句子、段落、章节中首尾呼应的修辞手法,递进、反转或交叉叙事的逻辑关系等。为了使译文既符合原文含义,又能让读者了解原文存在的语词或段落的内在脉络与暗示,还增加了译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自行查考、研读经文。
其翻译过程分为5个步骤 <2>,分别是:
1. 翻译初稿:由原文学者从原文圣经翻译初稿,撰写脚注;
2. 语文润饰:中文专家润饰译文,交译者修订;
3. 内部审校:内部审阅小组仔细校读,送特约专家审阅;
4.整合修订:译者整理各专家意见,修订译文和脚注,再交中文专家润饰;
5. 审批通过:专家主任最后审批译文。
我当时参与的工作有两部分:2012年底至2013年初,作为特约专家之一对已经修订完成的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进行文字审阅;2013年2月开始至2018年1月,以中文专家身份与一位希伯来语学者配合,对6卷历史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5卷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部分、《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3卷智慧书(《诗篇》部分、《传道书》、《雅歌》)的直译经文进行初步润饰,并参与部分经卷的再润饰。
在讨论方式与时间安排上,我与希伯来语学者在京港两地,通过现代通讯QQ和微信语音进行网上交流,每次集中对读和研讨直译的经文40句(如果出现疑难句式,会适当减少当天的讨论经句,按顺序延期),线上讨论每次不超过180分钟,以保证精神状态始终专注、活跃和饱满。
按照工作步骤要求,我会在希伯来语学者翻译过的经文基础上进行初改,而后,我们将对照其他中文和英文版本就每一句初改后的经文进行对读、盲听和再改,就字词的选用、句式的安排、语法规范、字句原义与语境及风格色彩等进行细致讨论,形成一个初步的定稿,提交给内部审阅小组。我们选用的对读版本包括官话和合本、官话和合本修订本(简称和修本)、新译本、吕振中本(简称吕本)、思高本、当代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等7个中文版本,YLT(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扬氏直译本)、NRSV(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修订标准本)和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新国际版)等3个英文版本,以及《CBOL原文字典与原文解析》提供的原文直译。
在版本对照和确定译文的过程中,除了前面提供的翻译原则,还有一条补充就是尽量避开与其他中文版本之间的重合,这既涉及到版权问题,也是对新汉语译本的直译方案是否能够有效推行的一种检验。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多数中文译本的文字表达都容易绕过,唯独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表达很难绕过。虽然“归结来看,和合本大约有4000多处的不足”,许多是因“当时,和合译本采用的底本主要限于其他英文译本,也以希腊文新约作参考,而且那个时候科技仍很落后,限于手工技术,排版校对易出错误” <3> ,但若论及各圣经译本对原文之忠实、选词之准确、用字之典雅以及影响力之巨,和合本的地位至今仍难以超越。
仅举二例。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