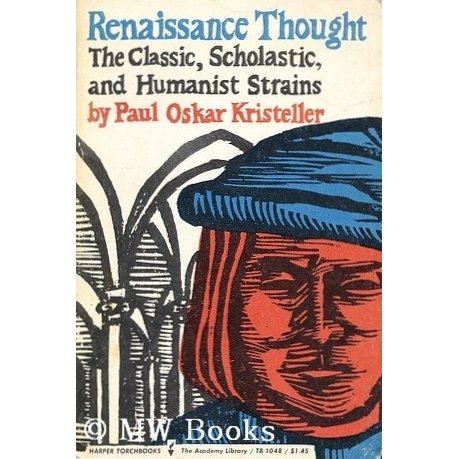
《世代》按:
本文为《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此书中文版权:橡树文字工作室)第一章第三部分中译本。《世代》已分享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第一章原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现代早期的归正宗传统 ”(From Reformation to Orthodox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第三部分原题目为,“方法与内容——再度澄清”(Method and Content—Once Again)。
作者:理查德·穆勒 (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荣休教授。译者:李晋、马丽。此部分编校:许宏。
译者按:
《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第一章前三部分,反映了西方世界近期对于宗教改革及十六、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澄清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翻译这篇,希望能够对汉语神学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规范。
就重新评价现代早期归正宗思想以及清除不乏问题的旧式主导式叙事而言,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在于对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做恰当的界定,也就是应当将两者视为思想史上的某种现象,或者具体来说,是中世纪及现代早期的学术文化现象,而非某种特定的神学或哲学。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一是现代早期的神学家们在阐述和提出各自神学时采用的方法,二是神学家们在基于解经、信仰告白、传统、哲学、背景而得出的结论——后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各自神学的教义内容。做出这种区分,是同时考虑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本身以及它们对改教者和之后新教作者的影响。当然,做出如此区分,不是主张方法和内容是可以全然分开的。这也并非否认方法和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如此区分的意思是说,方法(无论经院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并不产生特定的教义内容,例如,关于恩典的教义,既有奥古斯丁主义的,也有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的,也比如,还有形而上学控制下的所谓预定论体系。<33>
这点很显然——事实上,如果不是关于新教经院主义的旧式定义引起了显著的混乱,这应当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做评论。那些旧式定义仍在流行,特别是在支持所谓“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这样方法论的人群中。近来的一些著述,其中之一就体现了这样有缺陷的方法论。这些著述歪曲了上述区分,进一步导致了混乱。这些著述让人感到,上述区分似乎认为方法对内容没有任何影响。<34> 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注意,特别涉及将经院主义与预定论主义(predestinarianism)和宿命论(determinism)相混淆,以及将经院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混淆。这些混淆在“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文献之中很明显。
先看一个初步的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将经院主义主要定义为一种方法,具体说,就是学术方法,而非所涉及到的内容和具体的结论,无论神学还是哲学上的——这与将人文主义定义为一种方法很相似,具体说,就是语文学上的方法,也不涉及内容和具体结论——这样的定义不是出于反驳如下做法而采取的修正主义的学术立场,即对新教经院主义进行“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式的理解。这样的定义,其实是好几代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认同的方式,<35> 这样的定义在持有“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思想的学派对于经院主义进行教义上的重新理解之前就存在了。该学派论述加尔文及之后归正宗神学家的思想时,一般都忽视了这样的定义。换言之,将经院主义界定为主要是参考方法,这样的定义是把对新教经院主义和正统的重新评价牢牢置于思想史既有的轨迹之内,而“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学派以内容定义经院主义的做法是在历史真空中阐述的,这个真空被当代神学家的教义关切所充满。这个问题在主张“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观点更为近来的版本中尤为显著,因为在有关新教经院主义的问题上,这些版本相当有选择性地引用了修正主义者的文献,没有注意到涉及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本质的大量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是人们在修正关于现代早期新教思想看法方面一贯参考的因素。另外,上述版本也没有关注那些在对现代早期新教经院主义进行重新评价过程中分析过的材料。
简言之,这种”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定义假定,经院主义侵入新教神学,带来了各种形态的”演绎推论……都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奉之上”,并且意味着”对于形而上学之事、抽象的推理思想的显著兴趣,特别在关乎上帝的教义方面”,这种”与众不同的新教立场 ”被“塑造成基于对上帝旨意的推测性阐述之上”。<36> 这种论点也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将对于神学内容的理解分为经院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经院主义的脉络是亚里士多德主义、预定论主义、以及先验式的(a priori),在论证中甚至完全是三段论式的(syllogistic)——而人文主义的脉络则是反亚里士多德主义,它可能是柏拉图主义、圣约式的(covenantal),在论证中是后验式的(a posteriori)。<37> 以上二分法认为,是经院主义产生了“有限救赎”(limited atonement)、严格的预定论主义(predestinarianism)和枯燥的教义式神学,而人文主义则趋向于“普遍救赎”(universal atonement)、圣约式或拯救—历史的(salvation-historical)思想,以及圣经神学。 <38> 根据这种二分法,人文主义是加尔文思想中的推动力,产生了一种“平衡的”的神学,而不是一种体系,因为加尔文鄙视那种在他所在的时代被冒充的所谓”系统神学“——而经院主义则破坏了加尔文思想的平衡。<39> 这些主张不仅以各种整齐划一却站不住脚的二分法为特征,如将预定论主义对立基督中心论主义,预定论主义对立圣约主义,先验论对立后验论,有限救赎对立普遍救赎,而且所有这些人为的构建都是围绕着经院主义对立人文主义这个基本的二分法形成的,就好像历史能够被当成一排整齐的分类架来进行书写一般。<40> 这些观点还依靠相当奇怪的假设,即加尔文能够被放置在分类架的其中一个格子中,然后被用作评价整个传统发展的方便指数。而这种评价本身也是建立在对加尔文神学研究极度时代错乱的(anachronistic)方法之上,加尔文神学的现代教义倡导者却宣称,对于整个传统的评价来说,这是”完整和充分的主题“。<41>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历史性的问题:首先是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其次是方法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学者们对于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的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的历史研究已经表明,不应该将人文主义理解为经院主义之后的一种运动,人文主义是在艺术和语言研究中的一种运动,它开始于十三世纪,跟经院主义的兴起大约同时期,是与经院主义并行发展的。同样的研究也已表明,无论人文主义还是经院主义,都应当主要被理解为某种方法。<42> 然而,对于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历史以及两者在思想和课程上主要影响的重新定义,并没有减少十五世纪晚期和十六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与经院主义者之间辩论的影响,也没有缓解两者辩论的激烈程度。这种重新定义,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两者辩论的本质。<43> 这些”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文献,以阿姆斯壮(Armstrong)对于阿米若特主义 (Amyraldian)论辩的背景和表现的解释为代表,都倾向于假设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之间的分歧对于神学的内容而言具有巨大影响。而在对于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彼此间关系缺乏特定修正的情况下,这些文献也假设,在洛西林(Reuchlin)论辩所在的时代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之间的早期冲突,延续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改教者那里,并进入到十七世纪早期。<44> 换言之,上述文献对于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以及两者彼此关系仅仅提供了一种相当静态的理解。
学术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上述文献所说的那样。有理由说,在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的关系上面,有区分相当明显的阶段,也存在着大量具体而微的背景关系,<45> 有些要看主题领域和思想者所受训练情况而定,有些至少从恰恰被批评的角度而言,则受制于“经院主义”(scholastic)这个术语在使用时的变化。[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在现代早期,是没有人使用“人文主义者”(humanist)这个术语的]。在宗教改革之前,早期的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之间的辩论是在针对文献处理所用的方式及方法上产生的冲突,当时这些辩论大多发生在大学教职人员之中,很少直接跟神学相关。<46> 在宗教改革时期,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在于,人们在与经院主义神学家及哲学家辩论的时候使用了人文主义的方法,那些经院主义神学家和哲学家诉诸于传统上的权威,人们对此可以从分析古代材料的角度作出评论,这里的古代材料包括圣经的原始文本。当然,使用人文主义方法的评论者并非都跟宗教改革站在一起。接下来,那些宗教改革早期的辩论被这样的辩论状况所替代,神学家们开始改变辩论的背景,模糊辩论的界限,有些神学家最初是作为人文主义者接受训练的,其他的神学家带有比较传统的经院主义色彩——之后,辩论的状况又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经院主义展开辩论,尤其围绕名义上的经院神学和哲学的种类及时期。其中的辩论者要么具有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方法的双重训练,要么在更具人文主义的方法中含有经院主义的特征,或者在经院主义的方法中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方面。换言之,在神学和哲学领域中,以下两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是宗教改革之前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之间辩论的特征及行为,二是宗教改革发展时期及宗教改革之后的经院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
举例而言,加尔文的神学论证,显示出加尔文受到过人文主义的训练,但是也表现出明显的经院主义方法,<47> 跟有些现代学者的宣称不同,贝扎更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而非经院主义者,其关注在语言和文献学上,他只是具有某些经院主义论证的特点。<48> 截至阿米若特论战时期,几乎所有主要的归正宗作者都在语言方面具有人文主义方法的训练,比如,他们发表的学术演说还具有西塞罗式的风格,同时他们也在经院主义方法上接受了很好的训练,通过他们的辩论以及大量学术性神学著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非常具体的情形是,至少在这些神学圈子中,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方法之间的早期论战结束了,两种方法开始作为神学家们学术预备的共同基础。从加尔文的时代到十七世纪,对于经院主义者的攻击,是高度聚焦在学术神学的特定轨迹和教义结论的抨击上。这里区分两种经院神学,一种是比较古老的、让人接受的经院神学,另一种是比较新近的,中世纪晚期或罗马天主教的经院神学,有着颇具问题的神学轨迹。这里通常有一个前提,新教的“经院主义”方法并不受制于同样的批评。<49>
在经院主义中,就方法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而言:任何善于观察的读者,在阅读近期对于归正宗正统的修正性研究时,都会注意到在经院主义方法和教义内容的关系问题上引起的一些问题。就这点而言,方法和内容并非彼此排斥。有些研究具体显示了那些并非由方法产生的内容和结论,也有的显示了那些跟所采用的方法相关的内容。即使对于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经院主义方法或神学家们采纳的任何方法进行粗略的考察,就可以明显地认识到这一点:经院主义对教义上的结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结论当然不是“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学派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人文主义也同样如此。采取经院主义的方法并不会导致预定论或神人合作论(synergism)。同样可以说,使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四重因果论(fourfold causality),并不带来对形而上学的兴趣,更不用说带来形而上学的宿命论了。在神学上,人文主义并不导致对圣约的强调。将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与经院主义倾向联系起来,将他对圣约的理解跟他所受的人文主义训练联系起来,将加尔文进行如此分裂的做法是多么奇怪,多么不顾历史!将归正传统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院主义的预定论者,教导有限救赎,另一部分是相比之下较仁慈、温柔的人文主义者,教导假设性的普救论,这种做法是多么奇怪,多么不顾历史![可能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有两位人文主义者,坡博纳兹(Pietro Pomponazzi)和瓦拉(Lorenzo Valla),他们主张哲学性的宿命论——或者经院主义者如比埃尔、莫里纳(Luiz Molina)和阿米念, 他们则提出神人合作神学的不同样式]。对于十六、十七世纪的作者而言,经院主义或人文主义方法的存在,并非导致他们持有的预定论教义或圣约教义,或者就导致教义表述中的细微差别,例如某位思想者在关于上帝旨意的教义上,持有的是堕落前预定论,还是堕落后预定论。
方法对于何种内容有影响呢?对于采用经院主义方法的著作,就其学术本质和背景而言,现代早期的经院主义神学写作通常都会掌握和应用繁多的资料和技巧。经院主义传统呈现出对于诸如此类资料的显著运用:圣经文本;教会传统的资料,特别是主要教父的著作;古代哲学的主要著作;中世纪传统的论证轨迹;特定的信仰告白传统中前辈的著述;各样反对者的著作,无论神学上的还是哲学上的。现代早期经院主义作者使用的技巧,包括能够运用古典语言,特别是与文艺复兴相关的语言,并且要求在逻辑和修辞上受到过训练,能够掌握论证的模式。就论证中运用的资料及资料的广度而言,包括设定各种材料、资料和工具的相对权威性,经院主义论文的内容从方法那里吸取了营养。因此,在一部经院主义神学著作中,其内容不仅包括圣经的参考和使用,也包括不同教父、不同中世纪神学家、不同古代或更近时期哲学家著作的参考和使用——并且这些资料的内容将会对所写作品产生影响。但是,在表达了以上观点之后,辩论的内容和所获得的神学结论还是更多取决于材料的选择,以及作者个人的神学和哲学倾向,而非方法本身。
经院主义方法要求广泛掌握大量材料,包括肯定和否定意义上的,表述性和辩论性的,其中一些材料具有相对权威的地位。这样的要求使得我们需要考虑现代早期经院主义方法的两个相关方面,两者都根源于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其中之一明显受到文艺复兴辩证法或逻辑的影响——这两者是驳论(disputation)和立论(locus)。很大程度上,驳论是一种学术训练,就针对一个特定主题进行论证而言,与立论相关。而且,一系列的主题式驳论可以被置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部分,常常是论题或假设部分。在这里,原本的一系列学术训练,成为了一套神学立论(loci)的基础。论题或立论,如同驳论,是通过对于原材料的主题式解读而产生的,无论原材料是圣经,教父著作、其他传统材料,哲学议题,或是同代人的辩论。因此,很显然,这种方法的确影响内容,但是,却不是从所选具体题目、所强调的材料、或者所得出的教义结论而言的。
就像在别处证明的,这种主题式或立论式方法的影响之一,是强调主题的整体性或对主题的整体表述,并且弱化甚至反对包罗万象的教义模式的发展,诸如十九世纪神学所使用的那套演绎、系统性,和中心教理的方法。<50> 就整个神学而言,对演绎方法的反对是通过在因果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之间进行清晰区分而得以强化的(这种区分在十九世纪的著作中是缺失的):换言之,现代早期的归正宗神学家基于圣经论证诸如预定、呼召、信心、与基督联合、称义、分别为圣、得荣耀这类教义性主题之间相互的因果联系,与此同时,也会承认,这些主题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逻辑上从另外一个主题推演出来。因此,这是一种对于现代早期神学方法和资料的误读: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立论式的方法在确认和发展这些教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些关系已经在材料自身中显明或暗示出来。同样的错误是,看到那些如加尔文和布林格的神学家们没有将他们比较系统化的作品视为普遍立论(loci communes), 就以为他们不再受制于或以某种方式超越了主题式的方法。此方法的确对从一个立论到另一个立论的逻辑推演构成阻碍。(不然,就会像神学中的那个例子,从预定论或基督论或另外某个主题推演出其它教义)。而且,该方法论的问题,并非是将改教者们和后来归正宗正统作者分开的问题所在,也不是在对主题内容进行不同界定方面构成阻碍的问题所在,也非在主题本身互为相关的不同方式上构成阻碍的问题所在。对于救恩工作“链条”式的结构或因果关系结构的理解上,以及对于跟此因果关系结构相关的与基督联合的理解上,现代早期的发展昭示出,加尔文及其各样的同辈者,以及后来者的神学表述,都具有显著的共同基础,当然在各种主题和次主题的调用及其相互联系中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51>
在争论最为一般的层面上,方法是根据著作的类型和它所意图面向的观众,与内容产生联系的。考虑到这一时期的作者们在经院式(或学术)方法与流行大众、要理问答式(catechetical)、或解经式的方法之间有着一贯的分别——也在综合和分析的方法之间有分别——方法对文本的内容进行解释,涉及到细节的层次、格式、论证的种类、包含在内或排除在外的主题、以及各个主题的次序和安排。将“经院式”主要作为方法的标识,也因此与文本的类型相关,这种对“经院式”的理解是嵌在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的用法之内的。十六、十七世纪归正宗作者们的著述通常分为经院式的、要理问答式的和解经式的,他们将来自学术背景的作品视为经院式的。<52> 他们将有些作品界定为经院式的,而将另外一些作品界定为要理问答式的。在此方面,他们并没有认为,经院式的作品就会导致跟要理问答式作品不同的基本教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在细节的层次、定位和对教义的处理方式上。
某些主题和次主题出现在经院主义神学著作中,而没有出现在比如要理问答式的著述中,是考虑到这些主题和次主题面向的是学术上的受众。与此相似的是,要理问答式的著作则遵循跟经院式训练或辩论式处理不同的秩序和组织模式。“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理论中一个相当中心的要点,是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的预定论做了相对后验式或分析式的定位,同时与之相反的,是将许多十七世纪神学体系中的预定论做了相对先验式或综合式的定位。可以看出,这个要点跟定义上的不同或预定论体系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关系;此要点却与论证的不同做法有着诸多关联,论证的不同做法跟组织和教导神学的各种方式相关。那时的作者们明白经院式、要理问答式和信条式做法的应用,也明白在经院主义模式中更多遵循因果关系的做法带来的影响,同样明白在要理问答中更多使用分析式的“保罗神学”的做法带来的影响。在神学内容或教义含义上并不改变其观点的前提下,作者可以根据其使用的方法改变其定位,缩小主题的范围和减少细节,或者完全替换主题。<53>
虽然如此,更为经院式的阐述还是会具有清晰的论题式特点;建立清晰的、通常是命题式的定义或结论,按照逻辑去论证;提出并解决问题——这里的方法既没有决定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影响所得的结论。一种更偏人文主义式的阐释则更为散漫,倾向于修辞或劝导,与逻辑证明不同——这种方法最终也不会对主题的界定或论证的内容起到决定作用。考虑到著作的类型以及对细节的理解,当著作包含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某些差异时,方法的确会决定内容:例如,主题和类型决定其差异,这些差异引导论证的发展。尽管如此,考虑到经院主义方法及其差异的灵活性或中立性,<54> 这些差异本身并不决定论证的最终方向或结论。
经院主义方法影响内容,却不导致偏颇的结论。进一步说明这种方式的例子,就可以从经院神学和哲学的差异本质及其运用中找到。例如,上帝隐藏的意志(voluntas arcana)与上帝显明的意志(voluntas revelata)之间的差异,给关于神圣意志的教义内容加入了这个概念:神圣意志的有些方面是人无法获知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是人可以明白的——但是这个概念没有详细指明哪些是人无法知道的,哪些是显明的。神学家们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论证以下两者的关联:一是,三一上帝关于正义(justice)和义(righteousness )的内在(ad intra)神圣标准,二是,三一上帝关于律法的外在(ad extra)启示。神学家们同样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论证上帝的意志是出于律法的(ex lex)。当然,在区分有效的、正式的材料与最终的因果关系上,通过关乎基本原因或原由的内容方面的假设,因果关系语言的使用的确增加了以下的分析:有些是存在的,或者,某个结果还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不同原因的区分,并不导致对于原因的具体界定。所以,因果关系的语言既可以用来论证神恩独作(monergistic)的救赎论,也可以用于论证神人合作(synergistic)的救赎论,或用作对于圣经本质和特点的各样理解,等等。简言之,方法对于内容是有影响的,但方法却并非决定主题或教义的结论。
先前的神圣意志和后来的神圣意志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用来,也已经被用来解释阿米念的预定论教义,以及由归正宗假设性普救论者阿米若特(Moise Amyraut)所发展出来的非阿米念教义——并且,在限定之下,它也能够被那些更是归正宗正统的思想家使用。因此,就这些差异方面而言,与“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旧式理论所主张的相反,这些差异并非暗含一种“推测式的”神学。对这些差异的某些使用,是非常反-反推测式的(anti-antispeculative)。与此类似,在基督补赎(satisfaction)的完全与功效之间的标准差异,就像基督补赎的完成(impetratio)和应用(applicatio)之间的差异,也既能够被用来论证阿米念的立场,也可以论证归正宗的立场,在这里的每一个例子中,都带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在作为结果的事物(consequent thing)必然性和作为结果(consequence)的必然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在绝对必然性(absolute necessity)和可能性(contingency )之间的差异,既能够被用来支持自由选择,也可以用来反对自由选择。
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归正宗神学里,在界定经院主义方法的本质及其使用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不能高估经院主义方法对归正宗神学产生的影响。先前的学者,遵照阿姆斯壮很成问题的定义所隐含的意义,不仅倾向于将方法和内容以及结论混为一谈,而且也倾向于将归正宗正统的特点笼统称为“经院主义式”的,却没有恰当地认识到经院主义方法是限于神学著作的具体类型上,也不承认在所有写作的类型上,包括经院主义式的写作中,人文主义式的方法都具有深深的影响。一方面,无疑在(正如人们所想的)学术背景下,人们在那段时期对于经院主义方法的依赖是在逐步增加的,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具有肯定性和论辩性的神学立论的阐述中。另一方面,在其他学科如解经,其他背景如教会中,则会使用其他方法。经院主义的方法在要理问答中产生的影响很小,而要理问答教导的基本模式从宗教改革一直沿用至正统时期。相似的是,解经的基本模式,如语文上的的注释和神学上的评注也从宗教改革一直延续到正统时期。不仅是这些方法延续下来,人们还以追溯解释、论证和阐述的轨迹,这些方法也从宗教改革贯穿至正统时期。换言之,这一时期的评注、要理问答和讲道的神学内容,与较为经院主义的教义式的著作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互关系。这在基本教义的设定以及解经著作跟具体神学立论之间的建构性关系上都可以看出,这种建构性关系也延续到系统神学的论述中。也就是说,新教经院主义的兴起基本上不能被认为是后来新教思想发展的全部。
<33> 参考,不同定义上的陈述,见 Richard A. Muller, Christ and the Decree: Christology and Predestination in Reformed Theology from Calvin to Perkins, reissued, with a new preface (Grand Rapids: Baker, 2008), 第ix-x, 11-12页; 同上, After Calvin: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27-33, 74-78页; 作者同上, PRRD, I, 第 189-204页。
<34> 例如, Parte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第22页; 以及 Myk Habets, Review of Christ and the Decree,American Theological Inquiry, 3/2 (2010), 第107页; 以及我的回应, “Reassessing the Relation of Reformation and Orthodoxy—A Methodological Rejoinder,” American Theological Inquiry, 4/1 (2011), 第3-12页。
<35> 例如见,G. Fritz 和A. Michel的定义, “Scholastique,” in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ed. A. Vacant et al., 23 vols. (Paris: Librairie Letouzey et Ane, 1923-1950), XIV/2, col. 1691;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第92-119页; David 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第87页; Armand Maurer, Medieval Philoso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第90页; J. A. Weisheipl, “Scholastic Method,”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7), XII, 第1145-1146页; Calvin G. Normore, s.v., “Scholasticism,” in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ed. R.Aud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716-717页; 和 Ulrich G. Leinsle, Einführung in die scholastische Theologie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5), 第 5-15页。
<36> “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32页; 参见,同上,第120-121页。
<37> 参考,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120-121页; 和Jürgen Moltmann, “Zur Bedeutung des Petrus Ramus fü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im Calvinismus,”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68 (1956-1957), 第295-318页。
<38> 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140-141页, 151页; 参考,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第25-28页; Kendall, Calvin and English Calvinism, 第29-31页。
<39> 参考,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38, 129, 136-139页; 同上, “Duplex cognitio Dei, Or? The Problem and Relation of Structure, Form, and Purpose in Calvin’s Theology,” in Probing the Reformed Tradition: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Edward A. Dowey, Jr., ed. Elsie Anne McKee and Brian G. Armstrong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89), 第136页; 以及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第19-20, 25-26, 28页; William J. Bouwsma, John Calvin: A Sixteenth-Century Portra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 5, 238页, 注释 24; 作者同上, “The Spirituality of John Calvin,”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High Middle Ages and Reformation, ed. Jill Raitt (New York: Crossroad, 1987), 第318-319页。
<40> 例如,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120-121, 123, 127-129页, 等。
<41> 例如,Parte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第3, 4, 25, 27页。
<42> 参考,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第92-119页。
<43> 参考,对这些争论相对不同的评价, John F. D’Amico, “Humanism and Pre-Reformation Theology,” in Renaissance Humanism: Foundations, Forms, and Legacy, 3 vol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第. 349-379页; 和Lewis W. Spitz, “Humanism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ibid., 第380-411页; Charles G. Nauert, “The Clash of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An Approach to Pre-Reformation Controversies,” in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4 (1973), 第 1-18页; 作者同上, “Humanism as Method: Roots of Conflict with the Scholastic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9/2 (1998), 第427-438页; 和 Erika Rummel, “Et cum theologo bella poeta gerit: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Revisited,” in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3/4 (1992), 第713-726页. 这些叙述之间的不同之处——Nauert 肯定注意到这点——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人们所研究的人文主义的不同背景,尤其在Spitz 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背景和 Rummel 主要研究技艺中的争论。但是,这些作者都同意 Kristeller 的观点,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应当指涉的是方法。
<44> 例如,Armstrong, Calvin and the Amyraut Heresy, 第14-16, 38-41页及以后;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第25-26页。
<45> 参考,Nauert, “Clash of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第3-4, 13-14;页 和Erika Rummel, “Et cum theologo bella poeta gerit: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ists and Scholastics Revisited,” 第715, 725-726页, 他认为在十六世纪早期有激烈的争论,但是也指出要认识到“局部性”,“时序性”和“主题变化”的重要性。
<46> 注意此处观点,D’Amico, “Humanism and Pre-Reformation Theology,” 第 349-350, 353-355, 366-373页; 和Spitz, “Humanism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第393-395页。
<47> 参考,例如,Steinmetz, “Scholastic Calvin,” 第16-30页。
<48> Scott Manetsch, “Psalms before Sonnets: Theodore Beza and the Studia humanitati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Harvest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Heiko A “Oberman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Andrew C. Gow and Robert J. Bast (Leiden: E. J. Brill, 2000), 第400-416页; 论贝扎经院主义的局限,见 Jeffrey Mallinson, Faith, Reason, and Revelation in Theodore Beza (1519-16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67-70页。
<49> 见 Muller,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I, 第189-204页。
<50> 讨论见 Muller,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I, 第187-188页。
<51> Contra Evans, Imputation and Impartation, 第46, 52-53页. 论加尔文和立论方法, 见 Muller,Unaccommodated Calvin, 第29-30, 101-117, 119-130页。
<52> 参见 Muller,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I, 第189-204页。
<53> 见 Richard A. Muller, “The Placement of Predestination in Reformed Theology: Issue or Non-Issue?,” in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40/2 (2005), 第184-210页。
<54> 这是 L. M. de Rijk 的方法, Middeleeuwse Wijsbegeerte: Traditie en Vernieuwing (Assen: Van Gorcum, 1977); 法译本, La philosophie au Moyen Age (Leiden: Brill, 1985).
题图:
此文注脚推荐的一本专著封面。该书致力于还原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经院主义、人文主义。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译文,请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既有思想类文章,也有诗歌、小说、绘画。
《世代》第3期主题是“宗教改革”、世界观,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世代》并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