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图:2009年冬裴士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课。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2019年5月9日,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大学(Calvin University,前身为Calvin College)著名中国基督教史学者裴士丹(Daniel H.Bays)教授安息主怀。对于华人世界关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人来说,裴先生的名字大概不陌生,但论其为人治学、平素性情,恐非与之过从密切者难以体认。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泽汐专攻现代中国与基督教这段历史,且在留美期间与裴先生一家同住达五年之久,有机会亲炙先生风范。今先生辞世一周年之际,作者慨允惠寄纪念文章,从生平、学术和个人交往三方面向中文世界的读者介绍一代基督徒学人,并致哀思。《世代》编辑部在此谨致谢忱。
一 此生思君不敢忘
之前几度想作文纪念,但一提笔就心绪难平,终究默然。今5月9日即裴士丹先生(Daniel H.Bays)去世一周年,又正值新冠疫情流行,便安坐家中,从其生平、学术和个人交往勾勒我对先生的敬慕。以赤诚之心通古今,辨然否,温克令仪,文教远耀,先生实在无愧其名。
我的心哪!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圣经新译本《诗篇》42:5)
二 不入庙堂入学堂
Daniel Henry Bays, 对好友来说是Dan, 对无数受教的学生是Dr. Bays, 作为中国史学者是裴士丹,对与之度过51载婚姻的Janice Bays(我称简姨)是Honey, 对我来说是Uncle Dan(丹叔)。这或许已经反映了他生命的丰富。在丹叔少有的搞怪时刻,简姨也会配合地双手叉腰,眼如铜铃,以气势喷出丹叔的全名,“Daniel Henry Bays, what are you saying?” 之后便是哄然大笑。
丹叔在1942年3月27日生于密歇根州西南端的圣约瑟 (St. Joseph, Michigan)。坐看密歇根大湖,圣约瑟是个八九千人的小城。早在18、19世纪,由于水路便利,小城成为勾连北密(Michigan Upper Peninsula)、芝加哥、底特律的贸易站。除了大湖边的灯塔、夏天的淡水浴、二战后的婴儿潮,小城生活波澜不惊。游乐园中的过山车、舞厅、摩天轮并没有影响丹叔的学霸之路——他以同届第一名的身份致毕业辞,从圣约瑟高中毕业,拿到全额奖学金前往斯坦福大学。
作为社会运动与学术的前沿,北加州应该是丹叔开眼看世界的起始。在那里他加入了名为ATO (Alpha Tau Omega) 的兄弟会 (fraternity)。那时这些身披希腊字母、有着严格入会筛选和秘密考验的本科学生团体,应该还不似今日这般丑闻缠身。如今很多大学的兄弟会已逐渐沦为酗酒、嗑药和欺辱仪式的代名词;而在60年代初,这些旺盛的荷尔蒙似乎更多被用在搞运动上。冷战高峰的美苏对峙和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更加刺激了那席卷全球校园的左翼思潮。美国本土更是从50年代的民权运动一直烧到7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1865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内战后想以基督徒弟兄之爱弥合南北的老牌组织ATO,在运动中的斯坦福校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丹叔大一时,曾与斯坦福支部的成员一同投票选入四名犹太裔成员,欲以大学的非歧视立场挑战 ATO全国总部将成员限制于“基督徒白人”的章程。在理想蓬勃的年代,丹叔的眼光转向多元的海外(期间留学法国一年),同时却做了意外的选择:学习历史。
虽然斯坦福时期的一些课程已经激发了丹叔对中国的热情,但他在学术上转向中国史,应在60年代后期的密歇根大学。他也在那里拿到远东研究的硕士和亚洲历史的博士学位。“远东” (Far Eastern) 一词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国中心视角,而当时的丹叔也正在考虑自己是否要学以致用。若想匡扶天下、一展抱负,又何妨辅佐山姆大叔平定犬牙交错的“远东”呢?于是便申报美国国务院(职能上等同于外交部),一路过关斩将,百里挑一,终被录用。眼看调配在即,富贵可期,丹叔却最终放弃了国务院的任用。原来时值越战后期,诸多令人心惊的报道和图像,一经传回,激起千层浪。<1>丹叔自己的一位表兄也丧生战场。思虑之下,他认定无法为那些自己不认同的外交政策公开辩护。与其成为国家机器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不如知行合一贯彻另一种学以致用,即教授历史。感谢神,若非如此,我也无法与丹叔相遇,见证其基督徒学者的恩慈与风骨。
做不成外交官,丹叔1971年博士毕业就在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找到了教职。他很快组织起东亚研究中心,又两次被选为系主任。简姨曾跟我说,系里一位做犹太历史的教授行为不羁,时常搞出高价酒或晚餐之类的报销把戏。前几任系主任都选择息事宁人,而丹叔却不然。说话轻柔,为人内敛的他自有正气,在任内杜绝了上述资源滥用,虽惹来报复投诉也不改其志。信主后,丹叔夫妇更在自家带领国际学生团契,领很多堪萨斯大学的华人学生归主。
丹叔的学术也正发迹于此时。他于1973年获得国家人文基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去伦敦大英博物馆完成了对张之洞(1837—1909)晚年的研究,又在1977和1984年两次以福布莱特学者 (Fulbright scholar) 身份去台湾学习语言和宗教,更在大陆开放后就立刻奔赴学习。上海的田文栽老师回忆,丹叔1986年来金陵神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曾有面谈。所谈内容虽已无印象,但记得交流轻松,全无窒碍,可见其中文功力。之后丹叔简姨来往中国已不可计数,以致简姨对天坛附近的红桥市场如数家珍,砍价几乎不用我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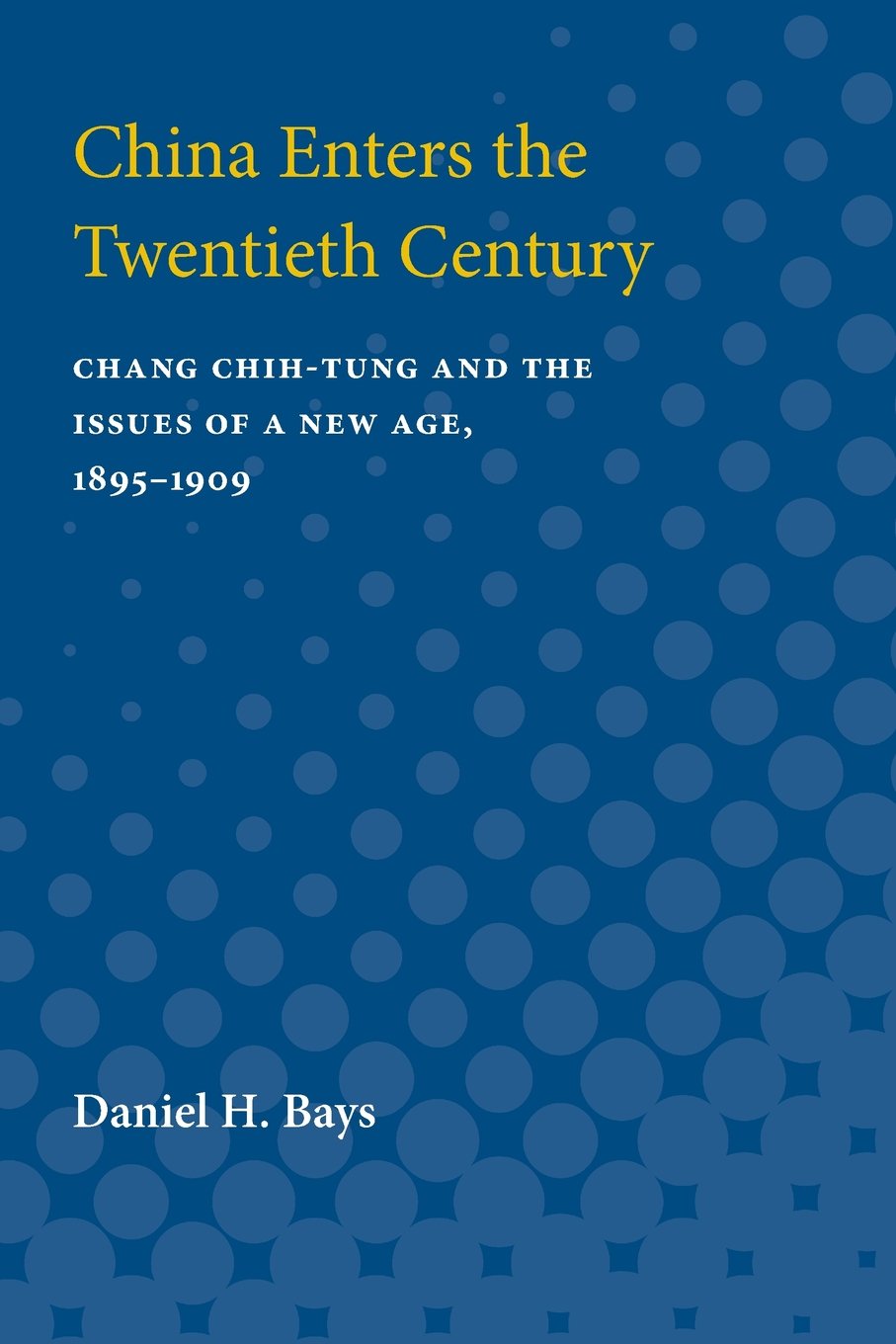
[插图1:裴士丹,《中国进入20世纪:张之洞和新时代的问题(1895—1909)》英文版封面。Daniel H.Bays,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6).图片来自https://www.amazon.com/China-Enters-Twentieth-Century-Chih-tung/dp/0472750186]
90年代也是丹叔的学术高产期,其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创见和影响,待下文一一述来。这里只消说他在2000年回到密歇根,受邀执教加尔文大学历史系(简姨常说是带着成堆的资金去的)以特别教席之身创立东亚研究项目。丹叔一边教课、带队学生往返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和北京,一面继续研究工作。鼎盛时期的加尔文东亚研究,历史有丹叔,宗教哲学有欧迪安 (Diane B. Obenchain), 中文有拉里·赫茨贝格(Larry Herzberg),哲学系亦有研究先秦诸子的教授,一时蔚然。而我也在2008年踉跄闯入,却不知那已是这鼎盛的余晖。
三 一入学海肆汪洋
话说1969年,“刘邓走资派”被打倒,毛重新掌权,林彪上位,文革如火如荼。大洋彼岸的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刊出了历史协会会长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1907—1991) 在几个月前年会上的演讲,题为“给70年代的作业”(Assignment for the 70s; 对,就是霸气,给全美历史学者布置作业)。其中费正清指出当时美国学界对基督教宣教研究的忽视,致使宣教士这一维系中西的重要群体成了历史研究的隐形人。考虑到宣教士与宣教机构常常保存有丰富的资料,为何不以此入手,探究现代中国呢?

[插图2: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 )肖像。图片来自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网站https://fairbank.fas.harvard.edu/our-mission/#our-mission]
宣教士沦为历史的隐形人,侧面印证了宣教事业在二战后的衰退。其实若细究传承,西方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汉学研究,都源于宣教士对自己的在华记录,以及与宣教相关的期刊、译著、专著。比如明清时来华的天主教修会,以及19世纪来华的新教先驱。1880年前后,美国大学陆续设立汉学教席,在华基督教研究开始呈现学院与宣教的双轨并行。其中代表是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1833年受美公理会差派来华,1877年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为全美先。他所创下的耶鲁传统,在赖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 身上结出果实。其1929年出版的皇皇巨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在数十年内是中国基督教史在英语世界的唯一通史类著作。或许耶鲁传统确实有注重通史的特点(赖氏两部后期著作也是动辄七卷、五卷本),赖德烈的晚年弟子马三乐 (Samuel H. Moffett,1916—2015), 同其师一般,身具学院与宣教两项事工,也写就两卷本的《基督教在亚洲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不过当马三乐在1955年被差往韩国时,宣教轨道对于在华基督教的研究业已式微。20世纪初各大差会纷纷撰写各自在华宣教史的火热场面已是历史。随着二战后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勃兴,反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横扫欧美学界,取代了相关科系对基督教和宣教的残余认同,被奉为一个时代的真理。70年代的耶鲁博士生,如今的世界基督教和宣教史大家黛娜·罗伯特(Dana L. Robert)曾跟我分享她求学时的艰辛。那些有宣教经历,教授宣教或基督教课程的老师,虽然被有跨文化经历的学生尊敬,但却被绝大部分人看做异类,不容于知识的殿堂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这也实在有趣。那些在宣教地(例如中国)形成的话语体系,诸如“基督教不外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类,兜兜转转,反在欧美大行其道,影响至今未消。耶鲁传统也一蹶不振,直到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的弟子唐日安 (Ryan Dunch) 出现。但那时已没有太多学统可言了。
二战之后几十年的美国,对于曾有双轨的在华基督教研究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萧条期。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佬费正清要在70年代给同期的历史学者布置新的作业。对费氏而言,宣教士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开拓者,对19、20世纪的改革和革命有前瞻性影响。经由他的推动和哈佛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一些针对在华基督教的研究开始出现。例如他所编辑的《中美基督教宣教事业》(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就包含柯文 (Paul A. Cohen) 写基督徒改革者和韦斯特 (Philip West) 写吴雷川(1870—1944)的论文,之后也分别被扩充成书。
但多数学者并未专注于在华基督教研究。如柯文和史景迁,他们首先是中国史学者,所关注之处不在于基督教,而是通过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与事件更加认识中国。哈佛传统所看重的理论框架,即“冲击—回应”范式,也首先发轫于费氏对中国现代化的解释。而后柯文的中国中心视角,和之后的全球化/去中心视角,以及对边缘群体的关注,都可以被看做对“冲击—回应”基础范式的修改和挑战,首先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真正以学院派的中国中心视角拓宽在华基督教研究的,正是丹叔。<2>也是在他这里,费正清的呼吁才真正开花结果。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宣教 (missions) 与基督教 (Christianity) 几乎是同义词,因而所谓“中国基督教” (Chinese Christianity) 在诸多美国汉学者看来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共产革命的胜利和50年代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难道不是已经宣判了基督教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失败吗?即便基督教在清末民初曾带来了一些知识和现代化意义上的影响,但其本质不外乎外国差会和宣教士,难以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主流——这岂不恰恰与“中国中心”相悖吗?
而丹叔却在1973年重新归主后就开始转而关注中国教会。他早期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就是基于中国语境,从仪式、小册子 (tracts) 和其他相似之处探讨晚清基督教与中国环境的关系。在费正清的鼓励和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丹叔在堪萨斯大学发起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这一研究课题 (1985-1992)。此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对宣教史的重新叙述悄然兴起,对非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历史的关注逐渐取代旧有西方中心的耀武扬威。以安德鲁·沃尔斯 (Andrew Walls) 为代表的一班学者正以全球的眼光重新审视基督教史,强调其作为世界宗教的跨文化影响和特征,和非西方地区教会的发展。也难怪丹叔(如他事后跟我分享)会闻沃尔斯而喜,因其重新从宣教、神学和圣经的角度将基督教史和区域史相勾连,使得中国基督教史既是中国史又是基督教史。在理论创新之外还有事实基础,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在宗教活动上的复兴。出乎众多西方观察者意料,共产中国数十年的政治运动未能从机构或个人的层面抹杀宗教;反而是八十年代对经济政策的放松和在国际关系上的重新构建,打开了宗教复兴的闸门。其中基督新教更是发展迅猛,信徒人数几乎已是1949年的十倍之重。悬念落下,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扎根无需外来影响。
对作为历史学者的丹叔来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探索这“扎根”(本土化)的源头、过程和挑战。1989年和1990年在堪萨斯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集众家之长,给我们带来了一本质量极高的编著:《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至今》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丹叔精选20篇论文,将其分为基督教与晚清社会(非常扎实的一节)、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与中国女性、中国本土基督教的兴起。最后一节尤其重要,吹响了在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本土化号角。丹叔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将分析和叙述的重心偏向中国基督徒而非宣教士,在文献的使用上偏向中文史料而非英文史料。这大概也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教会复兴给他的冲击,即中国教会兴旺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基督徒,宣教士的作用是间接的。
从90年代到2000年,丹叔的学术成果汪洋恣意。终于,神怜悯,他在退休之际完成了继赖德烈后英文世界罕见的中国基督教通史《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2012),作为他学术生涯的绝佳总结。全书在近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以凝练而权威的笔法,用八章涵盖了中国基督教史几乎所有的主要事件。其叙述宣教士的工作而不避讳他们与本土基督徒的张力,在着重本土教会的同时也并未将之理想化。秉承丹叔一直的治史理念,《新史》从中国教会出发,留意大的历史脉络,着眼个人在历史中的经历,不仅看到宣教士自明朝起数百年的播种之工,也看到中国的政治、宗教环境对教会的莫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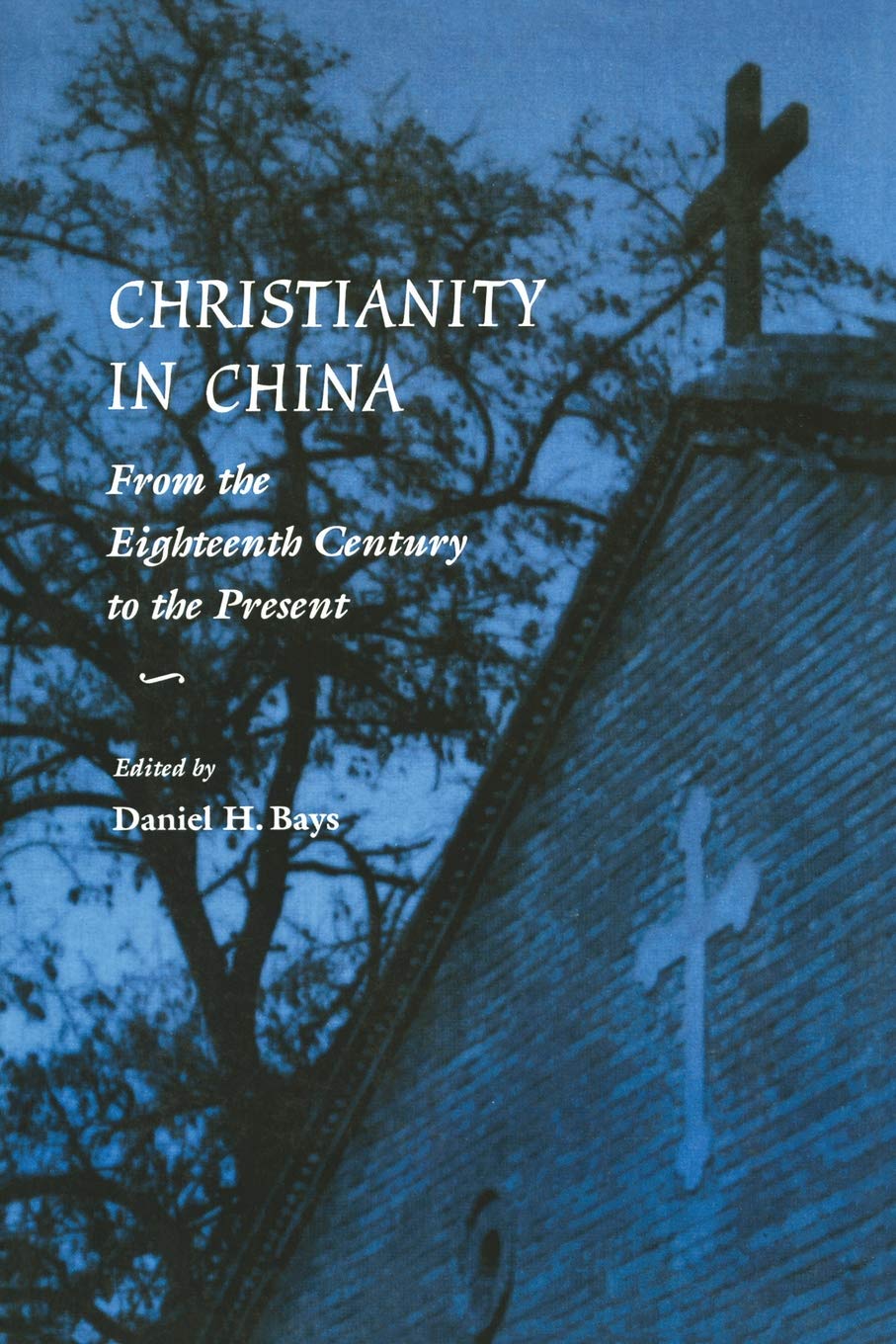
[插图3:裴士丹编,《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至今》英文版封面。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Daniel H.Bay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图片来自https://www.amazon.com/Christianity-China-Eighteenth-Century-Present/dp/0804736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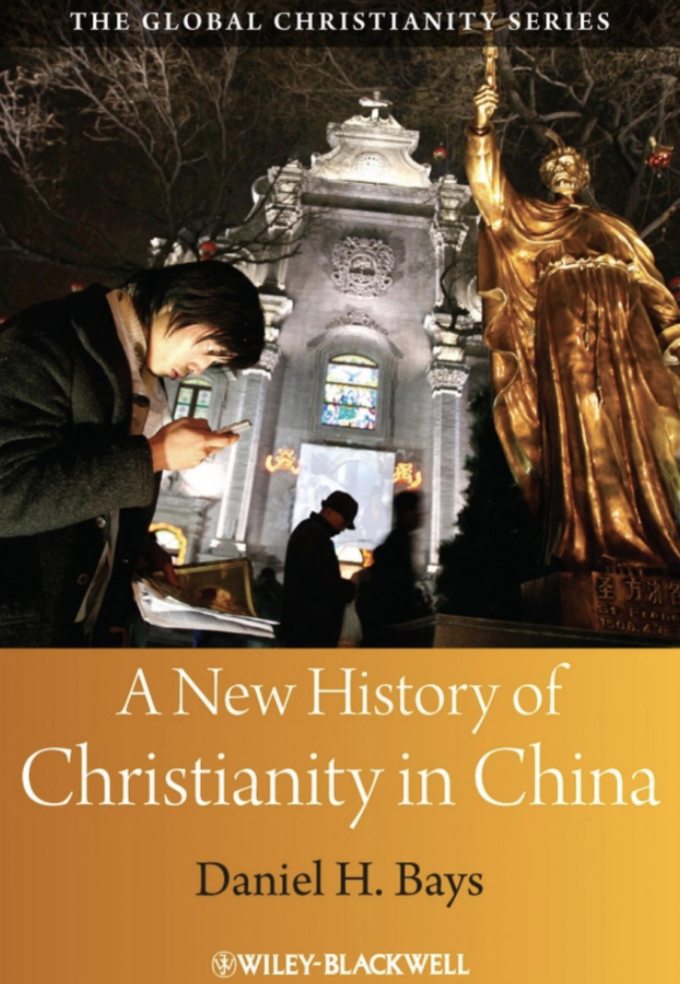
[插图4:裴士丹,《中国基督教新史》英文版封面。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Oxford:Wiley-Blackwell,2012).图片来自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lgS-j2m_0TEC&printsec=frontcover&dq=A+New+History+of+Christianity+in+China&hl=zh-CN&sa=X&ved=0ahUKEwit9u3mm6PpAhUPfnAKHdIyAr8Q6AEIKDAA#v=onepage&q=A%20New%20History%20of%20Christianity%20in%20China&f=false]
他学术写作的终章“反思新教与现代中国:历史分期问题”(Reflections on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 China: Problems of Periodization) 进一步点出中国基督教史中的三个重要角色:外国宣教士和差会、中国基督徒及其事工、中国政府及其要务;列出了三个大致的分期:排斥期(1807-90)、和解期(1890-1940)以及浴火重生(1950至今);结尾处更道出他所看到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基督教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强力国家政府的存在,其对宗教的管控,由清至今,几乎是本能性的,盖因朝堂历来便是被神化而带有宗教性质的权威来源。<3>我也以此为己任,继续梳理中国处境下的政教关系,和与大公教会传统的连接。窃以为,这当是中国教会认识自己、预备将来的重要功课。
四 月华流转松柏长
2007年8月,我满怀抱负与踟蹰,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来大急流城机场接我和父亲的,正是丹叔。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曾好奇地想,开着这辆旧车,言语柔缓,头顶凹陷,走路弓身的大个子,真的就是父亲口中的大学者吗?丹叔言语不多,但我总记得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Are you afraid of cats?” 这句话揭开了我之后与丹叔、简姨、两位猫兄弟五年的相处,和永远的亲情。
每个见过丹叔和简姨的人都会称赞他们是天作之合。丹叔静,简姨动;丹叔恬淡,简姨热烈;丹叔爱书,简姨爱琴;丹叔授学生以史,简姨待学生以饼干;丹叔总理账单和院子,简姨掌管厨房和采购——简姨很早就告诉我说,如果你丹叔问你饿不饿,你可一定回答不饿。其实丹叔还是有一手的。每次烤香肠和汉堡肉都是丹叔出马。
丹叔和简姨家是我走入的首个美国人家。第一印象是惊艳。一如其他几位恩待我、熟悉中国的加尔文大学的教授家,丹叔那里有历史和书籍的厚重,国画山水的灵动,琴曲乐器的优雅,青瓷碗碟的熟络,还有我为他们做中餐时,简姨会特别预备的中国菜刀和筷子。我不让她沾手,简姨就在一旁叨念,“Jesse you are incredible, your mom would be so proud of you.” 饭菜上桌时,丹叔狼吞虎咽,简姨则回忆起他们几十年前在台湾,首尝中餐就为之俘虏。“我们当时虽然没钱,但请的阿妈做菜真是厉害。”简姨总如是说。

[插图5:作者为裴士丹伉俪预备中餐。图片由作者提供。]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在丹叔和简姨身上看到的基督徒的生活。两人从未有过任何争执。这并不是说他们整日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岁月静好,十指不沾阳春水。相反,两人过着近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早上吻别后,丹叔就拿着准备好的午餐,晃悠悠的走去一街之隔的大学,简姨也开始一天的预备。但此中小到吃喝,大到帕金森,都从未在丹叔和简姨的关系上显出紧张。这是做不得伪的,我毕竟跟他们朝夕相处。 丹叔也会轻笑着说,“sweet heart, don’t be obnoxious”——这是简姨追问我在高中喜欢哪个女生。简姨也会作势叫道,“you smarty pants”——这是丹叔在快艇骰子 (Yahtzee) 这个游戏上力压我俩。
如鲁益斯(C. S. Lewis,1898—1963)所说,真正谦卑的人,不会把谦卑挂在嘴边,而是在言语和行为中好像忘了自己。感谢神,让我初来美国就见证这种谦卑。他们甚至不多谈自己的信仰,虽然他们待人之诚之爱,正是福音的果子。一次契机,简姨跟我分享她的信主经历。她小时候有路德宗的背景,但并不委身,在大学里更是喝酒如喝水 (“I was drinking like a fish”)。婚后第六年的一天,简姨如常回家停车。不想在和邻居攀谈、从后备箱取东西的时候,两位熊孩子上车放下了手刹。车开始下滑。她想冲回车上,但刹那间已被卷入车轮之下。那一刻,趴在水泥地上的她以为就要跟丹叔永别了。但那车的左侧前轮却奇迹般转过90度,错过她的头,在轧过后背和大腿后停了下来——她得救了。这事还上了报纸。自此以后,简姨成了重生的人。但她随即苦恼于不知该如何跟丹叔分享。那时丹叔对信仰并不感兴趣。
神已有安排。他们在这场意外后不久,就去了伦敦 (1973年)。终于有一天在早餐桌上,简姨忍不住哭了起来,坦言害怕自己将来在天上再也见不到丹叔。震撼之余,这成了丹叔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他开始读圣经,参加教会的查经小组,在研究题目上亦开始转向,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在学术领域和教会生活上的双重委身。感谢主,三十余年后,他们的爱与接纳,成全了神对初来乍到的我的应许:我在被围困的城里,他就向我显出他奇妙的慈爱。
我最终还是未能与丹叔完成一次学术访谈。他为什么选择在运动风涌的60年代学习中国历史呢?他又为什么要在冰封未解的70年代转向中国基督教研究呢?在80年代以降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基督教史与中国史和教会史的关系呢?在体味中国教会史时又该如何考量国家政治的因素呢?或许我确是入宝山而空手出;或许只是它们太丰盛,而我太贪心。
1996年,丹叔首次大病。他在简姨要去欧洲钢琴巡演的前两天诊断出脑瘤。万幸,肿瘤是良性,手术和术后恢复都一切正常。不想这却远非结束,乃是开始。那些起初促使丹叔去体检的微小症状,所谓“僵、慢、抖”,并未随着手术的成功而消失。最终医生确诊为帕金森病,丹叔也开始他与疾病争战的二十余年。我也目睹他身躯渐渐弓起,从还能自己开车,到走路要用拐杖,到将拐杖换成步行器 (walker),再到电动轮椅——这是怎样的折磨。然而身体的衰残没有掩盖他心灵的更新。我早上总能听到丹叔啊啊的做发声训练,有时还拿自己的笨拙开玩笑。周围的人从未听他对自己的病情有任何抱怨;他只是平安地接受自己,以及别人的帮助。
好景不长。丹叔还是在2013年正式退休了。他原本将退休地选在了最爱去的高尔夫球场旁边,但病情的迅速恶化使他们不得不搬入疗养院。待我在2016年感恩节携新婚妻子去看望他们二人时,丹叔的情况已经很不好。简姨数次流泪,却不敢在丹叔面前;丹叔看着自己最爱的饺子却无法送入口中,也不禁受挫流泪。但他依旧鼓励我,指教我论文投稿,和做丈夫的秘诀 (“admit it when you are wrong”),又坦言期待读到我的博士论文。

[插图6:2016年感恩节作者携新婚妻子看望丹叔和简姨,最后一次与丹叔会面。照片由作者提供并慨允发布。]
感谢主,直到最后数月,病情一直没有影响到他锋利的头脑。他在退休后依旧维持学术工作,用放大镜读书稿,再口述评论,由简姨在电脑上录出。但之后频繁出入重症病房终于为他在地上的呼召画上句号。丹叔在重症中曾说自己看到了三只小猫。稍后又说,我知道你看不到它们,但是我能看到——真是,幻视中尚有一丝清明。<4>
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因为主 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圣经新译本《启示录》22:3-5)
<1>参见1968年美军在越南制造的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1969年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大规模群众示威(Moratorium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以及1970年5月4日美国国民警卫队枪杀参加反对美军进入越南之抗议活动的多名学生,是为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等等。
<2>同期美国专治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寥寥,包括鲁珍晞 (Jessie G. Lutz)、狄德满 (R. G. Tiedemann,1941—2019),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罗恺玲 (Kathleen Lodwick), 张格物 (Murray A. Rubinstein) 等。
<3> Daniel H.Bays,”Reflections on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 China:Problems of Periodization.”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20.I,5-15,May 2013.
<4>丹叔和简姨育有一子一女。目前简姨的住所离她女儿较近,恳请各位祷告纪念。
2020年4月执笔于北卡家中
(作者简介:孙泽汐,2008—2012年就读于裴士丹教授执教的密西根州加尔文大学 (Calvin College, MI),现在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攻读教会历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与基督教,20世纪中国宗教与民族主义等。)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0期(2020年春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0期主题是“基督教世界观”,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