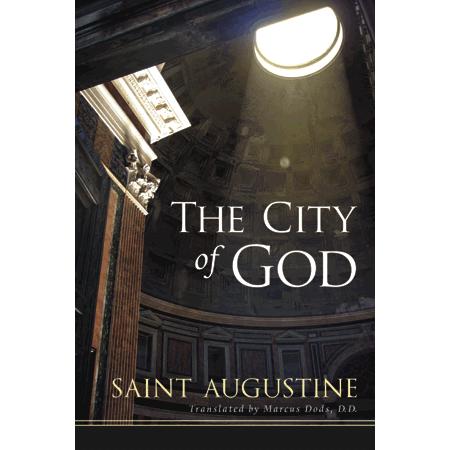
一
探讨中间阶层或者中产阶级这个话题,源于近来朋友间的交流。
在撰写《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中产阶级化倾向》前后,雪汉青说起她熟悉的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在经历近些年的生长后,正面临着中产阶级化负面影响的危险。
从雪汉青的观察来看,她所了解的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已经有着明显中产阶级的印记,如果教会不足够重视这个现象,中产阶级的特色就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特色,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或许就越发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论在哪种社会,身处这个暂时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世界,一向是基督教会及其成员不可缺少的特点。这决定了属于上帝永恒世界的基督教会及其成员跟暂时世界是处在张力之中的。<1>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那些容易视之为当然的方面,人可能不由自主地回避或消解这种并非来自人自己或这个世界的张力,以获得人自己的满足或这个世界的即时舒适或和谐状态,人之生存的真正活力也就随之消失。雪汉青所说的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中产阶级化倾向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现象也许就是人不自觉回避或消解张力的表现之一。
在雪汉青看来,上帝使用有中产阶级特征的基督徒群体推动了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建造,这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在教会公开化方面。
她所说的有中产阶级特征的基督徒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或有同等学力的基督徒,他们大多是社会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大致处于社会中间位置。1990年代以来,有着上述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背景的基督徒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比例显著增加。<2>
难以忽视的是,也正是在近二十多年,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同样增长显著。<3>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详见注释),2010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占全国人口将近9%,大约是2000年的2.5倍,1990年的6倍多,1982年的14.5倍;而2010年的中国总人口是1982年的1.3倍多。<4>
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2010年,中国大学(专科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接近614万人,而2016年应届毕业生大概760万。<5>
这意味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数显著增多,不是中国基督教会的独有现象,这跟中国社会的变化有着紧密联系。
在此背景下,很难说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不会受到中国社会的影响。雪汉青在文章中列举的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呈现的中产阶级化特征,可能至少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特点。
二
不过,就我自己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经历及观察,如果按照雪汉青使用的中产阶级定义,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与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相比还是有不同。
从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看,最突出的不同也许是,与后者相比,前者开始在某些方面比较敏感于自身跟所在暂时国家之间的张力。
这种敏感,部分源于中国家庭教会的内在传承,部分来自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所受西方教会及社会历史影响。这两方面的传承影响,在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表现明显。
从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看,如果没有以上传承和影响,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很可能跟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没有什么分别。通过在教会聚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面对圣经的这种双重教导——既有“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6>
这种双重教导,可以帮助身处社会各样位置的人看到,无论权力还是权利的来源都不是人,而是创造人和天地万物的神。无论人“顺服” “在上有权柄的”,还是“顺从神,不顺从人”,前提都在于承认上帝的主权。反过来,承认上帝的主权又是通过“顺服” “在上有权柄的”以及“顺从神,不顺从人”体现出来的。<7>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人士来说,这种看待社会秩序的方式跟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被教导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及流行文化有着明显不同。而无论是否有海外留学或生活的经历,他们如果在中国长期生活并在家庭教会聚会,官方意识形态及流行文化跟圣经教导的反差也是难以回避的。
如此的反差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这些言行伴随着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尤其在像北京和成都这样的城市。<8>
这些言行通过互联网为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一些人所知。近十几年既是中产阶级群体在中国显著增长的时期,也是互联网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兴起和普及的时期。
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受过高等教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通过互联网比较详细地表达和传递跟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言论,这已经成为日常现象。
在中国社会受过高等教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这种现象也并不很少见,但似乎没有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表现得突出,而且显然缺乏诸如上述既强调“顺服” “在上有权柄的”也强调“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的言论。
区分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并不在于其中一个群体本身就跟另一个不同。宽泛而言,这两个群体原来其实是一个。
1990年代以来,由于进入家庭教会或受西方教会及社会影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接触到跟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及流行文化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开始跟原来所在的中产阶级群体有了分别。
对于从受教育程度来界定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言,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可能是最体现他们受教育水平的方面。作为身处社会中间位置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群体,也许比社会其他阶层更有条件反思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他们没有处在社会的上层,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还有比较大的可能表达和传递跟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言论。他们没有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还有相对多的资源可以支配,还比较有可能在温饱之余选择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然而,恰恰是位于中间位置,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可能已经是或者希望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执行者,从而可能接近或进入社会上层。或者,他们并非积极拥抱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更接受流行文化或他们认同的思想观念。
面对官方意识形态及流行文化有独立思考的人可能历来都不会太多见。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一般情况下,从众或随大溜显然比独立思考更容易做到,也更容易带来安全感。<9>
在此方面,无论是以受教育程度还是收入状况界定,中产阶级群体对于安全感的需求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当今中国以及世界一些地方,安全感的需求与缺乏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特征之一。<10>
就在这种特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和西方教会及社会历史的影响给正在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之中的一些人提供了某种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可能提供的安全感不同。如果从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处境看,家庭教会很难给其成员带来中国官方正式承认的合法身份,也就很难带来受到政府保护的安全感。
但正是这种不来自暂时国家而来自既超越又临在的永恒国家的安全感,可以帮助中产阶级人士培养既独立思考又深入世界的生活习惯。这种离不开张力和警醒的安全感不是仅仅感觉上的,而是永恒国家进入暂时国家而带来的多方面生活上的真实体现。<11>
考虑到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在相对短期内比较快速形成的,他们在更长久时间的日常生活中如何面对来源不同的安全感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
尽管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晚近的现象,中国历史上,以受过高等教育来定义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群体并非到了近几十年才出现。
从1880年代到1920年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陆续在山东、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北京、湖北、湖南、福建、四川、天津创建了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西方形态的大学。 <12>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成为参与塑造现代中国社会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从他们开始形成现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当中也有人步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参与制定官方的意识形态。
在此期间(可能历来也大都如此),暂时国家的兴衰成败对于一般意义的中国人来说显然远更紧迫也更有吸引力。在关注暂时国家的中国人那里,传教士们及其建立的大学不可避免地跟西方世界的那些暂时国家捆绑在一起。
在此情况下,人们也就敏感于自己所在的这个暂时国家跟那些暂时国家的张力,而非这个或那个暂时国家与永恒国家的张力。在此背景下,由于后一组的张力弱甚至没有,人们所在的这个暂时国家拥有近似永恒国家的地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西方人进入明清中国以前,状况近似,当然也有不同。那时与现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接近的群体是“士”。
“士”作为一个显著阶层的兴起大约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的背景下,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使得原来位于贵族底层的“士”成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13>
“士”这个群体,春秋战国时也称为“士民”,与“农民”、“工民”、“商民”并列 <14>,后来更多叫做“士人”,总体来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跟“士大夫”不同,他们通常是没有官衔的读书人,“介于官民之间”。<15> 当然,他们跟“士大夫”并非完全不同,他们也可能成为“士大夫”。
至少部分受到所处社会位置的影响,“士人”的所思所想可能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完全一样。“士”被认为是“道”或文化传统的“承担者”,对官方的“势”或权力可以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制衡。<16>
“士”作为相对独立的阶层之所以能够兴起,跟“过去被垄断的思想权力逐渐分散”有着重要关系。春秋战国之后,这个群体还有比较显著的存在,基本也是在控制思想的权力经历相对分化的时期,比如宋明两代的一些时候,尤其表现为官学之外私学的某种兴盛以及城市、商业、传播技术的发展。<17>
但是,无论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官本位的局面大体没有实质的变化。
西方人比较大规模进入中国的19世纪,正是暂时国家的权威在西方增长的时候。那以前的一千多年,基督教会与暂时国家彼此分治又交织的状态,使得暂时国家的权威在西方受到比较明显的制约。但在近两三百年,随着西方人总体上不再像以往那样在乎圣经启示中的永恒国家,暂时国家或者暂时世界的吸引力就在显著增加。<18>
而就在西方人于20世纪中叶大批离开中国的几十年后,随着既是本土也是非官方的基督教会在中国城市的显著生长,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中的一些人开始关注圣经启示中的永恒国家。这些人在以前或许大多不曾想到这个永恒国家会跟他们有关。这也是中国官方于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出现的一个可能并非很多人都预料到的现象。
四
在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以及现代西方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如何进一步面对官方意识形态和各样的暂时国家、暂时世界,这可能是长久问题。
显然,教育是与此息息相关的重要方面。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之中的很多人出生在1960至1980年代之间,他们的子女很多正处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龄阶段。他们自己大多是在中国官办学校接受的教育,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导。
他们有的把子女送往海外读书,有的送到国内私立学校或有教会背景的学校,他们当中有自己建立学校的,从开办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也有开展在家上学的。这与传统中国历史上私学现象有相似之处,也可能让人想起西方传教士在现代中国之初的办学经历。
这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对待教育的取向也有关联。送子女到海外留学,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家庭近二十年来的突出现象。近些年,选择放弃高考而申请海外大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更低年龄阶段留学人数增长更为迅速。<19>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不再是1950-1970年代大部分时候被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那样。这不是说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就完全改变了。其实大约正是官方或有官方背景的人最早有条件将子女送到海外。能够去海外尤其是美国留学甚至工作定居逐渐成为不少中国人羡慕的生活。
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东周列国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当代翻版。<20> 这是西方人进入中国带来变化的继续。经历一百多年的冲撞和曲折后,中国人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总体上是将西方视为榜样,或至少是无法完全忽视的借鉴。即便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就是在如此氛围中形成的。这使得他们可以在西方塑造的现代世界中接触到传统中国或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的多样生活。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有机会了解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圣经和基督教会。
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信徒很多都将子女送往海外的基督教学校就读,这是他们跟中国其他中产阶级群体的不同之处。那些基督教学校大多不像中国人通常所谓的名校那么为人所知,却可能重视基督信仰与教育的关系。这可能体现了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没有被限制在中国官方以及一般流行的宣传当中。
与此相关的不同在于,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之中,不仅有下一代在海外基督教学校读书,也有不少人曾经或正在海外的基督教学校——尤其是神学院——学习或访问。
五
在这里,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人士需要进一步了解西方的基督教学校。西方或美国也是暂时世界的一部分。相比西方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今西方基督教学校总体处在衰落的状态,尤其缺乏神学院以外各领域研究生阶段的教育。<21> 这是当下及未来西方和中国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当今西方基督教学校缺乏神学院之外各领域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与近一百多年来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构成明显反差。<22> 这意味着,基督徒在完成基督教大学本科之后如果要在神学以外的具体学科进行深造,就要考虑去一般意义的研究型大学。
读研究生院并非深造的唯一途径,就读一般意义的研究型大学、各样的自学、工作,都可能有助于基督徒在多样的环境中探究基督信仰与所在领域的深入关系。但是,当今西方基督教学校缺乏神学院之外各领域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不仅事关学校教育,更关系到基督徒群体的教育水准和眼界及其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见证。
实际上,西方基督教学校并非一向缺乏神学院之外各领域研究生阶段教育。基督教会是孕育西方大学的母体。<23> 大学在11、12世纪的欧洲出现之后的几百年间,西方大学大体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运行的。<24>
在此框架内,神学不是唯一的专业,还有法学、医学,以及基础学科—自由七艺(文法、逻辑、修辞、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后来增加哲学)。学生完成基础学科,可以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通过深造可以取得博士学位。当然,那时的博士学位跟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是古典学意义上的,后者注重更为细分的专业研究。<25>
当今西方基督教学校之所以缺乏神学院以外各领域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部分是因为,很多原本跟基督教会或基督信仰有紧密关系的西方大学,在经历近一百多年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变的过程后,已经称不上是基督教学校了,而还称得上的或新兴的基督教学校基本都是本科学院。
在基督教学校和研究型大学都最为集中的美国,提供研究生阶段教育而且基督信仰比较浓厚的神学院是到了19世纪初才有的现象。这种类型当中最早出现的,是1807年创办的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它被认为是不仅神学也是任何学科意义上的美国第一家研究生院。安多弗的建立者是一位担任过代理哈佛院长的希伯来语教授及其支持者。他们从哈佛学院出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认同哈佛日益明显的“一位论”(Unitarianism)倾向。<26>
从那以后,正是哈佛、耶鲁这样后来为世界所知的学校开始从传统基督教古典学院逐步演变为研究型大学,而强调传统基督信仰且提供本科以上教育的神学院逐渐跟具有不同学科的大学分离。这有利于保持传统基督信仰的纯正,但是也使得传统基督教神学从一般意义的美国大学淡出,研究和分享基督信仰似乎只限于培养教会传道人的神学院,而神学院跟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及其专业的关系也就淡漠了。
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创立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安多弗神学院正是美国基督徒向国内及海外派出传教士的主要诞生地之一。<27>
类似哈佛与安多弗的历史,也在中国上演。比如,1919年,一位看重传统基督信仰的美国传教士从他参与创立的齐鲁大学出走,与他的支持者们建立了华北神学院。<28> 除了少数像华北神学院这样的神学高等教育机构,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大学,即使在1949年以前(甚至1927年前),很多已经跟传统的基督信仰没有多少关联。<29>
到了2010年代,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群体中,已经开始有神学院和学院建立起来。深入了解基督信仰与大学在历史中的真实状况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对于中国基督徒在各领域的深入见证至关重要。
六
学校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近些年,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各方面——除了办学,还有传统纸质书出版、互联网自媒体、商业、艺术等领域——创业的尝试都可能成为重塑教育的有益积累。
这群人似乎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从被动地消费由官方意识形态和流行文化主导的日常生活,到学习发现并分享上帝透过基督启示而产生的生活资源。
相比春秋战国兴起的“士”、宋明两代的“士人”或“士绅”、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这群人作为后来者似乎有更多反思和借鉴的资源。
但是,在20世纪各样革命运动熏陶的遗产中,在近些年各式即时成功学兴起的氛围里,当然还有更悠久的官本位传统的阴影下,当今的人们,包括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可能仍然容易受到语录体、运动式、崇拜个人或集体的文化感染,难以做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
比如,转发自媒体的文章已经成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细读,不难发现许多文章缺乏核实,以讹传讹的现象也就不鲜见。习惯顺手转发的人,不乏基督徒,他们似乎不太在意事实与否,而是易于被名人的光环或渲染的气氛吸引。
还有,在互联网上,包括基督徒发表文章时,使用不是自己写的文字,却不详细注明是引用别人,这样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似曾相识的文章不少,既有独立思考又有根有据的文章似乎不太多见。
又比如,每年问世的各种译作品很多,包括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但如果对照原文细读,翻译的质量普遍不高。这可能跟译者的外文和中文水准有关,可能是学校和社会上外文及中文教育水平不高的后果,也可能是因为翻译普遍不受重视,译者缺乏支持。
这些看起来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问题,却可能使得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在重塑教育的重要问题上停留在大而化之的阶段。
的确,在一些重要方面,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已经展现出跟一般中产阶级群体的不同。但是,考虑到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短期内在同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长成的,故两者可能都对关乎根基的细节问题缺乏重视。
或许,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可以从历史上那些做出关乎根基工作的人群得到借鉴。
基督教会在罗马—希腊世界兴起的几百年间,受过一定教育的中间阶层人士虽然不是基督徒群体的多数,却是解释和传播基督信仰的重要角色。这延续了犹太教的特点,其实是旧约和新约圣经及其载体——文字——重要性的体现。那些身处中间阶层、受过某种教育的基督徒有点像位于犹太人中间阶层的文士。<30>
从新约圣经的作者们(按照人的层面),比如使徒保罗 <31>,到后来对西方教会和社会影响深远的神学家们,例如特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5)<32>、阿塔那修(Athanasius,约295/299—373)<33>、哲罗姆(Jerome,约347—420)<34>、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35>, 他们基本都来自位于社会中层的家庭,这些家庭本身相对重视教育,他们成年后的眼界又比较开阔,因此得以在文字、思想方面打下承载基督信仰的厚实基础。
在罗马、希腊、希伯来等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这些人使用他们所在世界的通用语言和表达方式,在很多细节方面参与奠定了基督信仰在那个世界的根基。这个根基对于那个世界或任何暂时世界都是异质的。但是上帝却通过基督吸引并培育他们,将这个根基深入他们所在的世界中。
研究他们的成长历史,包括他们自身存在和面对的问题,会对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学习在中文世界打下类似的基础带来启发和提醒。虽然某种形态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但基督信仰的根基显然远没有进入到中文世界的深处。<36>
上面列举的人名仅仅是比较为当今世界所知的。在他们同时及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各自领域做出类似或不同的贡献。
尤其哲罗姆、奥古斯丁所在的4、5世纪之后,到宗教改革或归正运动(Reformation)所在的16、17世纪之前,有许多值得查看却被忽视的历史。如今依然有很多人根据普遍接受的教育,简单认为那一千多年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正是在那一千多年,西方更多接近如今受过高等教育意义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群体在教会与国家的张力中产生,这个张力使得教会和国家都没有完全取得统治西方的垄断地位,“顺服” “在上有权柄的”以及“顺从神,不顺从人”这类双重教导在日常生活中有相对可以落实下来的空间,诸如相对独立的城市或城邦和大学就是这种空间的某种体现,政治、经济、文字、思想、信仰方面的资源可以扩散到更多人那里。<37>
也就是在那一千多年,孕育了当今世人常常听说的所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各样政治革命运动。对于致力于重塑教育的人们,包括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人士,这些现象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许仍然处在语焉不详和缺乏反思的状态,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印象可能依旧是被官方意识形态和(包括小范围的)流行文化塑造的。
至少鉴于中国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多方面享有来自上帝的恩典,他们或许有责任学习在关乎根基的细节问题上还原被遮蔽的真实,而不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习惯中。<38>
这里所说的还原被遮蔽的真实,当然不限于对于西方的认识,也包括中国及其它。西方并非察看世界所依据的坐标本身,但是由于西方已经有关于上帝进入暂时世界而引发的丰富积累,也同样由于很多西方人对此的漠视,对西方的研究可以成为重新梳理中国及世界其它问题的借鉴。
七
根本上,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人也并非可以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里讨论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问题,不是刻意将人分为不同等级,而是借着人们日常谈论的现象,看看如何面对自己和朋友们共同遇到的问题。
对于本文作者而言,如果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说法在方便讨论之外还有什么价值,主要在于它所表达的中间状态。这是离不开警醒和张力的生命状态: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39>
<1> 参《马太福音》10:16;《约翰福音》15:19、17:14-16、18:36;《罗马书》8:9;《加拉太书》6:14。
<2> 关于这里所指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基督徒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的比例,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调查统计数据。但根据以下观察者或参与者的记录,可以看出明显增长的迹象: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 199-201; Li Ma and Jin Li, “Remaking the Civic Space: The Rise of Unregistered Protestantism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Urban China” in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edited by Joel A. Carpenter and Kevin R. den Dul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1-25; Brent Fulton, China’s Urban Christians: A Light that Cannot be Hidde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5), 41; Ian Johnson, “In China, Unregistered Churches Are Driving a Religious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April 23, 2017, adapted from Johnson’s book, 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 (Pantheon,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china-unregistered-churches-driving-religious-revolution/521544/。
<3> 有关中国高校扩招与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可以参考 Jing Lin and Xiaoyan Su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China’s Middle Class”, in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Cheng Li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217-244。
<4>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t20110428_30327.html;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0203/t20020331_30314.html;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0204/t20020404_30320.html;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0204/t20020404_30318.html。这里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1982年的公报中,“同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每十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416人上升为599人”,而在1990年公报中,“与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615人上升为1422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102/t20110228_30025.html。
<6> 参《罗马书》13:1;《使徒行传》5:29。
<7> 参《彼得前书》2:13;《使徒行传》5:27-32。
<8> Promise Hsu, “Public Theology in China: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ChinaSource Quarterly, June 26, 2015.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public-theology-in-china.
<9> 参《出埃及记》23:2。
<10> 在谷歌及其它搜索引擎键入“安全感”和“中产阶级”,会看到很多讨论。
<11> 参《撒母耳记下》24:14;《历代志上》21:13;《马太福音》6:7-13、24-34,7:11;《路加福音》12:11-34;《腓立比书》4:18:19;《雅各书》2:14-16。
<12> 详见杰西·格·卢茨著, 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英文原版: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1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9-82。
<14> 《管子·小匡》:“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http://ctext.org/guanzi/xiao-kuang/zhs。《春秋穀梁传·成公元年》:“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http://ctext.org/guliang-zhuan/cheng-gong-yuan-nian/zhs。
<15>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217。
<1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0,98,100-101。
<1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71-272,299-302。《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http://ctext.org/chun-qiu-zuo-zhuan/zhao-gong-shi-qi-nian/zh。《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 http://ctext.org/shiji/li-shu1/zh。
<18> 西方人对此早有各样反思,可以参考近来的一本比较易读的专著:便雅悯·瓦克,《敬拜国家:自由主义如何成为我们的国家宗教》,Benjamin Wiker, Worshipping the State: How Liberalism Became Our State Religion (Regnery Publishing, 2013)。
<19> 王景烁、张宇、高四维,《绕开高考独木桥》,《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9日。http://zqb.cyol.com/html/2014-06/09/nw.D110000zgqnb_20140609_1-07.htm。叶雨婷,《调查显示:我国低龄留学人数增长迅速》,《中青在线》,2016年10月22日。http://article.cyol.com/news/content/2016-10/22/content_14345873.htm。
<20> 参见注17。
<21> 乔治·马斯登著,许宏译,《美国大学之魂》,《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George Marsden,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First Things, January 1991.
<22> Louis Menand, Paul Reitter, Chad Weldon, eds., 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ourceboo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Julie A. Reube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3> Walter Rü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ume 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xix.
<24> Geoffrey Blainey, 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180-181.
<25>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04.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 Robert S. Rait, Life in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137-138.
<26> Margaret Lamberts Bendroth, A School of the Church: Andover Newton Across Two Centurie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xi, 6-16. Roger L. Geige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Culture from the Founding to World War I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1-142. Samuel Eliot 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Belknap Press, 2001), 187-191.
<27> Wilbert R. Shenk ed. , North American Foreign Missions, 1810-1914: Theology, Theory, and Polic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4), 12. Margaret Lamberts Bendroth, A School of the Church: Andover Newton Across Two Centurie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xi.
<28>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第三版)》(汉塞尔出版社,2017)。
<29> 许宏,《教育之真相: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信仰分歧及其影响浅议》,《杏花》(2013年秋冬合刊)。
<30> W. H. C. Frend,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Fortress Press, 1984), 26, 30, 310.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The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Before A.D. 170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3), 57, 162.
<31> 参《使徒行传》18:3,21:39,22:3。
<32> 参 Geoffrey D. Dunn, Tertullian (Routledge, 2004), 3-4。
<33> 参 Khaled Anatolios, Athanasius (Routledge, 2004), 3-4。
<34> 参 Stefan Rebenich, Jerome (Routledge, 2002), 4-11。
<35> 参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3-28。
<36>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
<37> Brian Tierney, 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1-2. Henri Pirenn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 XVI Century, translated by Bernard Miall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2010), 45.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translated by Frank D. Hal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84-109, 125, 138-152. 这里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中世纪城市:起源与贸易的复兴》英译本,使用“middle class”(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陈国樑中译本,《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译为“市民阶级”。爱德华·格兰特著,张卜天译,《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2-15,45-67。Edward Grant,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Their Religious,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9, 33-53. Frederick B. Artz, 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s: An Historical Survey, A.D. 200-15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26-228, 314-319, 320-323, 356, 361, 446-452. Robert Gilp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tate: Critical Concepts, Volume 2, edited by John A. Hall (Routledge, 1994), 536-537. 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69-70, 117-122. Morris Bishop, The Middle Ages (Mariner Books, 2001), 240. Norman F. Cantor, “The Essential Threefold Paradigm: Nobility, Church, Middle Class”, Medieval Reader (HarperPerennial, 1994), v.
<38> 参《申命记》4:32;《诗篇》111:2;《传道书》7:25、9:1;《路加福音》1:3;《约翰福音》21:24;《歌罗西书》2:6-10。
<39> 《箴言》30:7-9。参见《世代》第2期另一篇文章:许宏,《鲁滨逊为何漂流》。
题图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2009年英文版封面(Hendrickson Publishers)。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