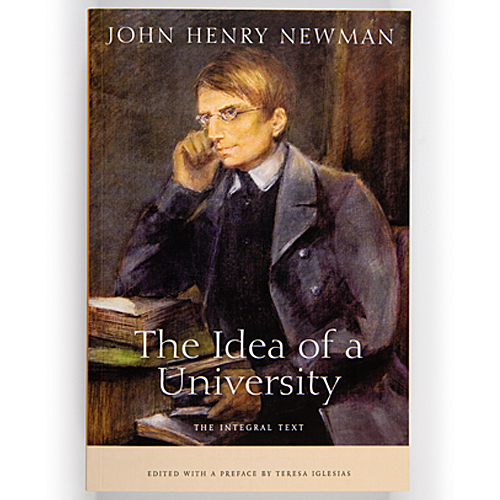
《世代》按:
此文原来题为《基督教研究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意义:从纽曼的“大学理念”说起》,发表于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145—158页:http://cscsnet.hkbu.edu.hk/articles/he1_f.html。经作者允许在此转载,此处略有改动。
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文章本身也可能成为做进一步反思的历史素材。
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大学的经历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它们经历过世界大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震荡: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的拆散或肢解、合并或拼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系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大潮中的膨胀或扩张、联姻或吞并;从“土地改革”时创办革命干部大学,到“文化革命”初期的全面停课、中期的下乡务农和后期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全国的高等院校都大起大落,在劫难逃。另一方面,它们又维持着也许只有前苏联的大学才可以相比的长期不变:从教育理念到管理体制,从教学方法到教材体系,一代又一代的教师都相沿成习,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也习以为常。
当然,这两个彼此相反的特征,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全国统一的教育体制和领导人的即时意愿。
然而,在世纪交替的这几年,由于相当多的学生、家长、教师尤其是一些官员的思想转变或曰“思想解放”,中国大学的渐进的良性转变已初露端倪。除了经济发展导致的大学地位提高和教师收入改善之外,各大学在管理、教学和教材等方面的自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些方面的所谓“国际接轨”进程也有了加速的迹象。<1>
在本文所注重的教育理念方面,虽然较之前述几个方面而言转变不甚明显,但是也有了实际的进步,这特别表现为“素质教育”这一口号的提出,这个口号相比于前三十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相比于实为政治灌输的“德育”和分数挂帅的“智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其全面彻底的实施,还需要人们——首先是教师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种努力,理应包括对于国外重要的教育理念的思考、评价和吸纳。在这方面,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的“大学理念”,无疑是很值得思考的。
一、纽曼的“大学理念”之再思
1
作为一位活跃多产的著作家,纽曼不但以“牛津运动”的核心人物著称,而且以一种大学理念的倡导者闻名,不但以其在“时代书册”中发表的文章和改宗行为引起了一时的轰动,而且以其在《大学理念》一书中发表的演辞和办学主张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他在应邀主持筹办爱尔兰第一所天主教大学期间,发表了五次系列演讲,后来又写作了另外五篇演讲稿。1852年,他把这十篇演辞结集出版,题为《论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在担任该大学的校长期间,他还为哲学与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专门写过十篇演辞或文章,1859年以《论大学课程》为题发表。1873年,他把这两本书修订并合集为《大学理念之界说与阐明》一书出版,从此,这部在他死前已再版九次的著作,便以“大学理念”之名传世。
这部名著在1996年作为西方传统“关键性著作”系列之一再版时,丛书编者之一、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兰克‧特纳(Frank M. Turner)在“前言”中写道:“纽曼的《大学理念》在其出版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之中,对于高等教育的相关探讨和概念形成,一直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现在,高等院校及其课程设置、使命天职、资金筹措等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在这样一个时代,耶鲁大学出版社在其 ‘再思西方传统’丛书中再版这一经典著作,诚为适时之举。纽曼的著作深深植根于这一传统,反过来又对理解这一传统并向一代又一代学生传授这一传统的方式,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所谓理解和传授一种传统的方式,也就是教育的方式。在中国大学的教育方式真正要“面向世界”的今天,如果中国真正要走进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那么,再思一下纽曼的“大学理念”,看其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有何参考价值,可以说也是一种“适时之举”罢。
2
在这部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形成和目标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中,纽曼讨论的重要问题非常之多,以至于要在此一一探讨,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就其主要观点与我们的论题之间的关系,作一点粗浅的“再思”。
纽曼的一个观点,是认为大学应被界定为“传授全面知识的地方”。<3> 他解释这个观点说:“这意味着其宗旨一方面是智力性的而非道德性的;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假如大学的宗旨在于科学发现和哲学探索,我就看不出它为什么要有学生;假如意在宗教训练,我也看不出它何以能成为文学和科学的中心。” <4>
在此应该澄清的是,这里的“道德”一词毋宁说是“宗教”一词的误用。因为,纽曼在后面多次通过说明教皇建议设立这所大学的目的的方式和其他方式,表达了对道德或品性培养的重视,例如他说:教皇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不是科学、艺术、文学、职业技能和知识发现本身,而是要借助文学和科学,使他的子民受益;……使其在某些道德或智力习惯方面得以践行和成长。” <5> 他还在提到“英国绅士”这一概念的狭隘性之后,肯定了大学培养“绅士”的目标。<6> 同时,他还多次区分大学的教育职能与教会的宗教职能。他认为大学是一种人间的机构,应该造就具有广博的知识、批判性的思维、高尚的道德和社会敏感性的人。大学不是能从根本上转变人的堕落性和罪性的机构,但是能够通过开明的或文科的学问来塑造纽曼所谓的绅士。
纽曼认为,大学教育从定义上说就有别于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大学教育要达到的目标,是视野的开拓,心智的转变、思维的习惯,以及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的能力。
但在另一方面,纽曼又认为,所谓全面的知识当然应该包括神学,因为神学也是一门学科(他称之为一门科学或科学中的科学)。他论证说,一个机构若不教授全面的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也就不能称为“全面的学校” (university)即大学。<7>
纽曼还强调了大学与科学院(academies)或学会(societies)的区别。他认为后者“主要关注的是科学本身而不是学生。” <8> 他指出:“发现与传授是不同的功能;二者也是不同的禀赋,而且很少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一个人耗费时光向所有的来者传播其现有的知识,就不大可能还有余暇或精力来获取新的知识。人类的常识已将对真理的探索与宁静隔绝的状态联系起来。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都专心致志于他们的主题而容不得打扰;他们往往神不守舍,性格独特,而且或多或少地避开教室或公共学校。” <9>
总的来看,纽曼的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大学有别于职业性或专科性的学校,主要任务不是进行职业培训或专业教育,而是通过开明的或自由的或文科的学问,<10> 扩展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的思维,转变学生的习性,“使他们成为更聪慧、更能干、更活跃的社会成员。” 一句话, <11> 大学的目标是培养他所说的“绅士”。
二是大学有别于科学院或各种学会,其主要功能不是进行科学的探索或发现,而是向学生传授已有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传授也并非为了科学发展本身,而是为了学生的培养。
三是大学不同于教会或宗教机构,其任务不是转变“堕落的人”或罪人,而是通过哲学、文学、科学等的教育,使学生能在“堕落的人类社会中”生活,并具有“权宜性的、世俗的美德。” <12> 但是,大学传授的知识应该是“全面的”,所以理应包含基督教神学。
3
在“再思”这些观点,考虑其中每一个部分之适宜与不适宜,可取与不可取的时候,我想,以当代中国大学的状况作为立足点,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大学中“素质教育”的状况,来思考纽曼关于“绅士教育”的观点。
正如纽曼假设的他的听众对“英国绅士”的批评一样,他的绅士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显然也是不适宜的、不可取的。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教育曾经彻底地、有时甚至是非理性地(如在“文革”之中)批判了与普通民众对立的贵族思想或贵族作风,从广大人民的观念层面扫荡了“绅士”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社会生活的等级性阴影在民众下意识层面中的负面影响,依然不可低估,这种影响在最近十来年中已经浮现于社会的表层,助长了生活中的诸多不公平现象。 <13> 考虑到这种社会现实,关于“绅士教育”的提法,即便有某种高尚的因素内在于其中,仍然是不可取、不适宜,同时也是行不通的。
然而,从前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纽曼的观念中有不少东西十分接近于当代中国大学中关于素质教育的观念。这种教育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学校长期以来一直以片面的政治灌输取代全面的人格培养,以技术性的智慧(尤其是记忆能力)培养取代精神性的人性熏陶。这种教育也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教育中的这种缺失,现在已经将恶果撒向了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使得追求真理的精神日益淡漠,同情仁爱的品质日益少见,自我中心盛行,犬儒主义成风。凡有鼻子可嗅的人,都可以嗅到这些恶果腐臭的气味!
然而,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提出好些年了,其效果距离中国社会的需要之遥远,是不可否认的。原因固然很多(首先是学校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远远不及其他方面的制度、传媒及其造成的行为表率的影响力大),但我想,未能认真地思考和吸取国外行之有效的某些教育理念,也许可算为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究关系的状况及其得失,来思考纽曼关于“传授”与“发现”的观点。
一方面,纽曼以后一百多年的大学发展,包括苏联大学与科学院分离的模式和美国以大学为科研基地的模式,从整体上说似乎反驳了纽曼的论点,因为美国模式已经赢得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成效。另一方面,不论是在美国、苏联,还是在中国,甚至在任何别的地方,大学和科学院里的实际状况也告诉我们,许多人确实在“教学”与“科研”所需的两类才能中只具备一类,或者一类远胜于另一类,这使得他们在某一类机构中不能够人尽其才。一种失败的制度,也就是不能让尽可能多的科研人才搞科研,教学人才搞教学,让两种才能皆有者人尽其才,让两种才能皆无者改换职业的制度,即相对不合理的制度。
就当代中国大学的状况而言,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科研职能在从科学院转向大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于僵硬的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在大学内部仍然有上述相对不合理的制度存在。<14>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仅就教学工作,或者仅就学生培养尤其是素质培养的工作而言,纽曼的观点自有其道理。换言之,教学固然有助于科研,但仍然会占用科研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对科研能力较强或两种能力均强的教师来说,仍然会减少科研成效。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纽曼的关切,主要是在教学或“传授知识”或培养学生方面。
纽曼的论述还提醒我们,应当注意科研工作或他所谓“发现”工作的精神层面。当代中国大学中众多学者的状况表明,长时间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有时候会使研究者专注于或有志于或献身于某一领域,这会对学者本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之更有可能做出较大的贡献。而在另一个极端,对其研究物件完全冷漠的学者,因为对其领域没有精神上的投入,其研究成效一般也较小。而这在当代中国的大学里并非罕见的现象。
最后,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大学内学科设置的状况,来思考纽曼关于“全面知识”的观点。
当代中国大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本来就是专科性的,或者是从专业学院扩大而成的,例如林业大学或医科大学之类;另一类则是所谓“综合性大学”。前一类大学的学科设置,当然与“全面知识”相去甚远。<15> 后一类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有较全面的课程设置,但是由于院系之间的壁垒,不但不像西方一些大学那样要求学生必须学习跨系科课程,反而对学生的跨系科学习有所限制。<16> 再加上学生必须归属某一系科,所以对于学生来说,综合大学的实际状况不那么“综合”,学生所学知识也不那么“全面”(universal)。
同本文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是,中国的两类大学之中不论哪一类,自19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都没有神学课程的设置。当然,纽曼所说的基督教神学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的教义阐释,因而不但当代中国大学没有设置,像美国这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也没有设置,尽管欧洲国家多有设置,一些国家如德国还在同一学校内设置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两个神学系。不过在美国,由于在公立大学之外还有许多基督教团体开办的私立大学、宗教学校和神学院,所以学生要学习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宗教知识,都仍然有很多途径。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大学在这方面仅可说是刚刚起步。在中国,政教分离的原则当然应该维护,甚至还应该进一步阐明真义并真正持守。而这意味着在保障宗教徒与非教徒权利平等(包括政治权利和教育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政治和教育不受宗教干预,也不干预宗教。因此,纽曼所说的那种从信仰出发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在当代中国大学中也是不适宜、不可取的。
但是,就从理性出发的基督教研究而言,把它作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纳入大学课程设置,显然是促使大学知识更加全面的努力中必要的一步。现在,已有少数综合性大学在宗教学系课程设置中走出了这必要的一步,这是必须肯定并予以推进的。
二、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之特点
1
基督教研究与基督教神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二者有联系,是因为基督教研究必然包含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否则就不但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缺乏头脑”的。因为,如果说基督教的历史、礼仪、教会等等的研究是着眼于其“四肢”,那么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就是着眼于其“头脑”。说二者有区别,是因为基督教研究是从理性出发,从外部向内部的探索,而基督教神学是从信仰出发,从内部向外部的阐发,前者是纯粹学术性的,后者是学术性与信仰性兼具的。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不但从逻辑或本质上说属于学术研究,从历史或事实上说,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
从历史上看,中国真正的基督教研究,大概可以从明末与耶稣会士交往的士大夫说起。且不说许多士大夫只是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感兴趣,并不真正信奉基督教,即所谓“宗其学而不奉其教”或者“阳奉其教而阴尽其学”,<17> 即使是真正信教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至少在起初也是在相当的距离之外,抱着儒家式的实用理性态度来对待基督教的。这种理性的、因而是接近学术研究的态度,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直至今日,一直是绝大部分研究基督教的中国学者的重要特点。
这里的原因十分明显,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传统进入另一种传统后的互动关系,而一种传统中的人群要吸纳另一种传统中的某些因素,首先就需要解释或广义的翻译,解释或广义的翻译又需要理性的研究。对一个传统悠久和学者主导型的社会而言,更是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承担解释另一传统的职能或工作的中国学者,不可避免地会把其知识分子的“知识性”或“理智性”(intellectual)特征,带到这项工作中来。
2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的理智性和学术性特点,在20世纪前期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传入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是理性的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同中国传统的理性考据方法是可以契合的。 <18> 因而,民国初年的基督教研究,一方面是以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同基督教的比较角度为主,另一方面是以历史考证角度为主。 前者显示出某些比较宗教学的理性特征,而后者则显示出宗教史学的实证特征,两者当然都具有理性的学术研究的性质。
3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断之后重新兴起的基督教研究,总的来说是由教会外的学者发起和主导的。这些学者主要来自各级社会科学院和各地大学,而且原来的研究多在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学等学术领域。他们全都生长在无神论的环境之中,自幼受到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强烈熏陶,所以,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少是倾向于理性主义的。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大学中的基督教研究,总体上不能不具有理性的学术研究的性质。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融入现代国际社会,因此也必然会更多地具备现代化社会的两大特征,即政教分离和宗教多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学的基督教研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依然会是一种理性的、学术的研究。即令在思想观念多元的大潮之中,从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从理性出发、以理性为工具,坚持研究的学术性质,也依然会是中国大学中基督教研究的首要特征。
三、基督教研究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意义
1
在前述的两类当代中国大学中,第一类即专科类大学,显然极需走出专科、专业或职业的狭窄范围,争取用本学科以外的广阔得多的知识去丰富学生的头脑。这不但是教给学生更“全面”知识的需要,甚至是使学生在本专业之内得到提高的需要。因为在这个科际融合的时代,专注于本专业的思想方法本身,更是十分过时的。
第二类即综合性大学,如前所述,也面临着时代挑战——走向真正的“全面”、“综合”的“大”学(university),也就是使自身名符其实,使自己“大”起来。这里所谓“全面”、“综合”和“大”起来,不是对校长而言的,因为一个大学对一个校长来说,总是够大的,甚至太大了──头绪万千,日理万机。这里所谓“全面”、“综合”和“大”起来,乃是对学生而言的,因为一个大学对一个学生来说,总是有那么多陌生的地方,那么多陌生而威严的老师,那么多令人神往又令人生畏的学科──在系里是条“龙”,在校内是条“虫”。这里所谓“时代挑战”,是说在这个普及教育的时代(我不大愿意说是“素质竞争的时代”),至少本科生教育必须更多地趋于“通才”教育而非“专才”教育。否则,我们也许会比纽曼的19世纪还要落伍。顺便说一句,相对而言不太重视专业教育的英国,竟然产生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至少是值得思考的。
当代中国大学这种走向真正的“全面”、“综合”的需要,向学生传授“全面知识”的需要,意味着基督教研究对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很明显,所谓“全面知识”的“全面”(universal),理应包含对于普遍(universally)影响了文明进程的基督教的认识;所谓“综合大学”的“综合”(comprehensive),理应包括探求理解(to comprehend)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基督教的这种研究。否则便谈不上“全面”、“综合”的大学,对学生而言尤其如此。
即使只看所谓“专科大学”也是如此,我们且以林业大学和医科大学为例。在今天,前者必须讲授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后者也应该讲授身心医学的谘询问题。如果分别增加一些西方环保中的基督教观念影响的知识,<19> 增加一些西方社会中的教牧人员心理谘询工作的知识,<20> 无疑会提高学生在相关课题上的专业造诣。
现在,鉴于少数综合性大学已经开始设置了基督教研究学科,从而使其学科配置更加全面,更加同国外著名大学接近,并由此而增加了国内外大学的学术交流,我们还可以说,基督教研究已经对当代中国大学的良性发展,做出了明显可见的贡献。
2
就当代中国大学内的科研工作而言,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它都应该立足于社会的现实状况,应该为总体的社会发展服务。
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基督宗教在“假死”至少20年之后的急剧增长。这个事实具有多方面的实际影响,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放眼也应该纳入科研视野的世界局势,则基督教不但在过去两千年中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而且在过去五百年间也深深地影响了国际社会,至今也依然对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是考虑到我们科研工作的立足点,还是考虑到其目标,它都理应包含对基督教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基督教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趋势,及其在思想、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
还可以一提的是,基督教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和多学科的研究,它不但需要进入人类历史中各大文化圈和各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需要采用哲学的、神学的、思想史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现象学的、语言学的等等诸多不同的学科方法。因此,它对于当代中国大学中尚待发展的对同一主题的跨文化研究和多学科研究,预期可以发挥某种示范或促进作用。
当然,这种研究,作为这一学科教学工作的基础,也是同当代中国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教学发展相辅相成的。
3
最后,我们可以看看基督教研究同当代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关系。
素质教育无疑应侧重于精神层面。因为它所要矫正的,首先应是那些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倾向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潮流;它所要培养的,首先应是正直、诚实、勤奋、仁爱的精神品格。一个受教育者,只要摆脱了那些倾向潮流,具备了这些精神品格,无论具有其他什么观点和兴趣爱好,无论在某些方面的才能是高是低是强是弱,都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自己能够健康生活、又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公民的基本素质。一句话,这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起码要求。
然而,每一个教育者都知道,要达到这个“起码要求”,真是谈何容易!它不但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和长时间的协同努力,而且需要教育者自身多方面和长时间的精神修养。
精神层面的教育,需要对人类文明之精神核心的领悟。因此,通过客观理性的或学术性的(即非主观盲信的或灌输式的)研究和教学,将人类文明之精神核心揭示给学生,使之从中受到启发,汲取精神营养,对于素质教育可以说是必不可少。
在此,我们不难看到,以基督教研究为基础的这一领域的教学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大学中的素质教育所具有的意义。因为,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历史悠久而又能适应不同时代精神需求的基督教,在人类文明中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毕竟,如果纽曼可以说:“当教会建立一所大学时,它之所以珍视才能、天赋或学识,并非为了这些东西本身,而是为了它的子民,所着眼者,乃是他们的精神幸福” <21> ,那么,我们建立这么多的大学,难道不也应该以此为目标吗?
<1> 至少就“重点大学”而言,学校人事制度增加了灵活性和自主性,教学方式逐步多样化,教学成果评估逐步规范化和民主化,开始注意教材国际化或采用国外先进教材,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加等等,都是这些方面的明显迹象。
<2>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 F. M. Tur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ix.
<3> 同上,p. 3。
<4> 同上。
<5> 同上,p. 4。
<6> 同上,p. 6。
<7> 同上,p. xiv。
<8> 同上。
<9> 同上,p. 5-6。
<10> 这三个中文词在英文里是一个词,即“liberal”。
<11> 同上,p. 5。
<12> 同上,p. xv。
<13> 当然,这些现象中很大一部分同对“贵族”或“绅士”概念的完全无知或荒唐歪曲有关联,即完全不懂得其中的温文有礼、遵守规则、宽宏大量甚至见义勇为等精神因素。于是,从“包二奶”、“包三奶”的暴发户可以自命为某种乡绅,到庸俗低级的高消费行为也竟然自命为“贵族气派”,这类怪现象也就比比皆是了。
<14> 近闻清华大学将为教学和科研人员设立三种不同的职位,让前述四种类型中的前三类能够人尽其才。但笔者尚未获得权威来源的证实。
<15> 但其中有一些学校领导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补救措施,例如开设一些“素质教育”课程,或举办一些讲座,以增加学生对专业以外知识的了解。
<16> 限制的程度当然是因校而异的,有些学校较多,有些则较少。
<17> 参见朱维铮,〈序〉,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上海古籍,1998)。
<18> 前者主要由吴雷川、赵紫宸、谢扶雅等教会内的学者进行,后者主要由陈垣等历史学者进行。
<19> 从《创世记》中的“利用”到“看守”即“管理”自然的概念,这种影响甚大。
<20> 这种工作不但在实践中对公共卫生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甚至对精神病学和心理谘询理论也有很大贡献。
<21>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 F. M. Tur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
题图为纽曼《大学理念》2009年版封面,来自http://www.ucd.ie/news/2009/10OCT09/151009_newman.html 。
此文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