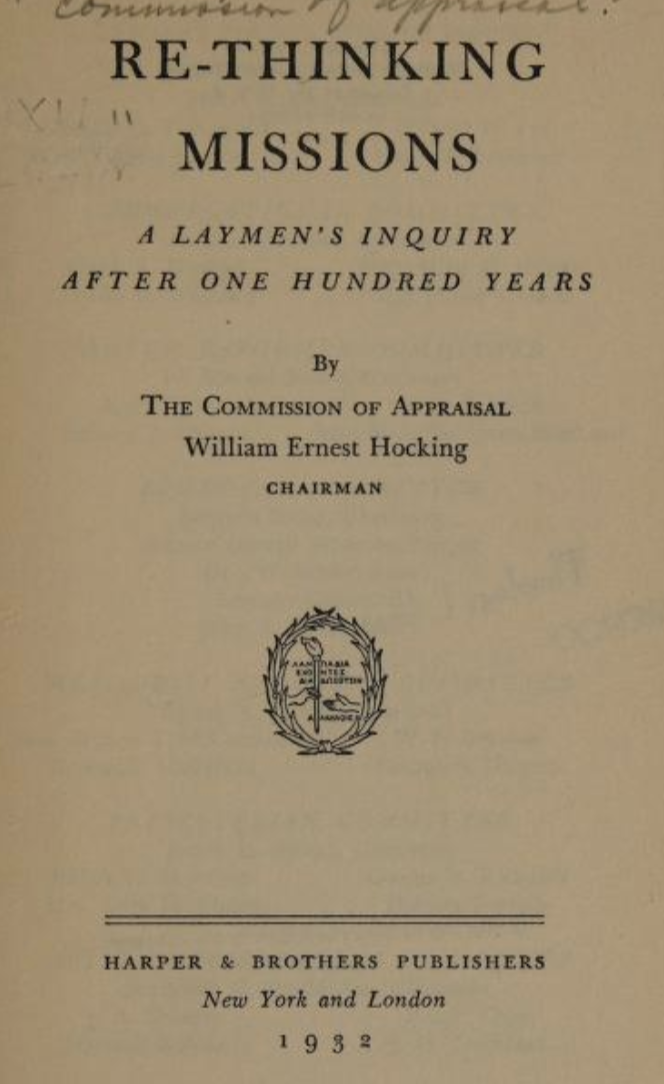[题图:《宣教事业平议》(1932年)英文版扉页]
摘要:二十世纪初见证了基督新教内部的自由派神学与基要派神学之争。1932年出版的《宣教事业平议》(Re-Thinking Missions: A Laymen’s Inquiry After 100 Years)再次引发广发辩论,而这场辩论亦波及中国。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最重要的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于接下来的一年内,刊登了诸多讨论该书的文稿。这些文稿,赞同该书观点者有之,全然反对该书观点者亦有之。本文首先重构《宣教事业平议》产生的历史语境,然后以《教务杂志》对该书的讨论为中心,揭示不同神学立场的作者如何评论该书,尤其着重分析关于该书之性质的不同理解,以期还原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派神学和保守派神学之间,这一场最激烈且精彩纷呈的论战。
关键词:《宣教事业平议》、《教务杂志》、自由派神学、保守派神学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
——《圣经·箴言》27章6节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一、楔子
1915年来华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士、上海沪江大学的教员普天德(Gordon Poteat,1891—1986),曾在1933年说起自己有一次与一位中国基督徒教师一起讨论出版不久的《宣教事业平议》(Re-Thinking Missions: A Laymen’s Inquiry After 100 Years,以下简称《平议》;此外,该文献在历史上也被称为Laymen’s Report,即《平信徒调查报告》)。这位基督徒教师头脑聪明,很委身于基督信仰,他评价《平议》一书时说道:“《平议》说,宣教工作必须有所变化,对吗?那么,《平议》若让人们开始讨论并思考这变化,就很有价值了;毕竟,事情若再像以前那样,就无法再持续多久了。”普天德回应道:“在美国,很多人正为了所传给东方人的基督教信息(the Christian Message to the Orient),而激烈辩论着。”这位中国的基督徒教师却回答说:“这个我们不担心;因为,得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信息是什么(what the Message is)。”按普天德的看法,这位中国的基督徒教师的态度,乃是受到中国文化“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立场分明,而是持“让我们讨论看看,或许双方都有可取之处”的态度。<1>
的确,1932年出版的这本重要的书,所引发的辩论,如洪水决堤一般。这些辩论,不仅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西方宣教士所居处的东方宣教地,其中当然包括了这本书极为关注的东方大国——中国。在这里,宣教士最重要的期刊、常被认为神学“自由派”之领地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紧跟时潮,1933年全年讨论《平议》的文稿,为数甚多。其中,态度鲜明地表示赞同者有之,全然反对者有之,为后人生动地呈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派神学和保守派神学之间,一场最激烈且精彩纷呈的论战。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在重构《平议》产生之历史语境的基础上,以《教务杂志》对《平议》一书的讨论(1933年)为中心,旨在揭橥不同神学立场的人对《平议》一书所进行的多元、且时常尖锐对立的评论,并集中分析关于《平议》之性质的不同理解。
二、语境重构:《平议》的缘起
从1910年至1933年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共有三件大事,构成基督教宣教事业的里程碑。它们分别是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1928年的耶路撒冷国际宣教会议,以及本文所探讨的1930—1932年的“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不过,尽管这三个事件在宣教史上相当重要,但是即便在基督徒的圈子里,爱丁堡会议的报告没有带来多少反响,耶路撒冷会议的报告也只是比前者好一点。而三者之中,最见效果的是“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精华版《平议》一书——它在基督教的圈子内外,均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作为这三大里程碑之一的《平议》,<3> 源于1930年美国一些“平信徒”(有文章对该运动中“laymen”这个术语能否精确表意提出质疑<4>)发起的海外宣教调查。1930年1月,一些美北浸信会的平信徒认为,有必要对西方国家百年来更正教宣教的“根据、目的及活动”进行调查和反思,并邀请其他宗派参加。最终,有美国的七个宗派(包括北浸、公理、美以美、长老、圣公、约老及联老)的非正式代表各五人,组织了“北美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研究会”。调查的范围限定在印度、缅甸、日本和中国四个宣教地。调查为期两年,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其一,“用科学客观的方法,搜集材料”,以便作为下个阶段“评审的根据”,这一阶段从1930年年末至1931年9月,由北美社会宗教研究社组织调查;其二,根据前一阶段调查得出的宣教事业的状况,与当代世界的情形,对宣教“作一番审慎的估定”。后一阶段从1931年9月至1932年9月,由15人组成的、受委托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再赴前述被调查的宣教地作考察,并最终起草《平议》一书(此书最终在1932年11月正式出版)。<5>
《平议》的内容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平议》绝非对宣教事业的完全客观中立的调查与评估。换言之,该书的产生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即所谓的自由派神学立场。这一点,可以从与“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以及《平议》一书的撰写有最直接关系的两个人的生平可以看到: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1874—1960)和威廉·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1873—1966)。作为此次“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发起人和资助者的洛克菲勒,其所在的教会,是作为二十世纪自由派神学之代表的牧师、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的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在纽约牧养的浸信会。<6> 洛克菲勒这样的信仰背景,反映其偏向自由派神学的立场。的确,他亦曾经在191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会:未来在何处?》(The Christian Church: What of Its Future?),表达对保守的更正教过于强调教义的不满——这不过是回应19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的自由派神学。<7> 尽管这篇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海外宣教,但是可以算作“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先声。后来,美北长老会的基要派健将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反对“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调查和评估结果时,就指出,《平议》是由一位自由派的平信徒(说的正是洛克菲勒)资助的,而这位平信徒曾经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主张,不用承认任何信条,就可以加入教会。<8>
霍金则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宗教哲学教授,同时亦为公理会的平信徒。在“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第二阶段,他担任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并撰写了《平议》的头四章(第四章是他与另一位贵格派信徒合写)。<9> 霍金曾在1912年写过《人类经验中之上帝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这一部算是更正教的自由派传统的“小型经典”(minor classic),其神学自然偏向自由派立场。<10> 因此,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争论激烈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一位学者所撰写的宣教议题,自然引起保守派基督徒的反击。确实,无论是从西方国家中的讨论,还是从《教务杂志》中的讨论,都可以发现,正是《平议》中霍金所写的、分别题为“普通原则”(第一章)、“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及非宗教”(第二章)、“基督教对于远东的使命”(第三章)、“宣教事业的范围”(第四章)的头四章,产生了最多的辩论和尖锐的意见冲突,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平议》一书的争议焦点。<11>
究竟《教务杂志》中的文章,如何评论《平议》一书,尤其是如何评论头四章的内容?对立的表态、观点或论证又是如何在其中呈现出来?本文第三节将分析《教务杂志》对于《平议》的整体态度,以及其中对于《平议》表示赞同之态度的文章;第四节则分析《教务杂志》对于《平议》持反对意见的官方声明以及文章。最后一节尝试将《平议》的文本与那些反对意见进行对照,考察这些反对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
三、“朋友加的伤害”?
(一)《教务杂志》对于《平议》的整体态度
1933年全年共12期的《教务杂志》,讨论《平议》的篇幅非常多,实为该期刊的编辑大力鼓励的结果。第2期的编者言中,临退休的代编辑麦金铎(Gilbert McIntosh)清楚表明,希望有宣教士就《平议》进行“阐释”或“建设性地批判”,亦避免“刻薄的争辩”。<12> 这份编者言,透露出的是客观中立的姿态,认为只要是建设性的研究,赞同的或批评的阐述都是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已经有宣教士表达对《平议》的不满和反批判,可是代编辑麦金铎又不愿因这些辩论而造成“不必要且不幸的分裂”,所以引用《圣经·箴言书》27章6节,称《平议》对宣教事业的批判,是“朋友加的伤害”;亦即,撰写《平议》的这些委员,是宣教士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此《平议》的内容如果伤害了宣教士群体,那也是“出于忠诚”。<13> 无论如何,麦金铎发出一种力图平衡对立观点的讯号。
但是,从第3期开始,《教务杂志》编辑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1871—1937)休假归来,重新执掌期刊事务。这位美南浸信会的前宣教士从1914年开始成为《教务杂志》的总编辑,<14> 却与其所属的保守派差会渐行渐远,并为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现代的民族主义所说服,最终接受了自由派神学的立场。<15> 于是,在《教务杂志》第3期的编者言中,乐灵生完全站在(从他自己的神学立场则是可以理解的)赞同《平议》的立场上,提醒所有传教士,不可以“陷在怨恨和自我防卫的情绪中”;对《平议》中的批评,最好的回应就是“自我省察”。<16> 虽然乐灵生也承认,没有必要把《平议》看为必须完全接受或完全否弃,<17> 但是他整体的态度,是“对于仅仅是为了否定《平议》的文章不感兴趣”。所以,《教务杂志》第5期有一位读者苏梅克(J. E. Shoemaker)在致该刊编辑的通信中,指责第3期的编者言给人的印象是:现在开始,《教务杂志》就成为了“一个以党派性宣传为目标的机构”(an organ for partisan propaganda purposes),只是为了推销《平议》中提出的计划,一点也没有留余地给那些不同意《平议》神学观点的人。苏梅克希望,《教务杂志》既能给赞同《平议》的人留版面,也同样能给反对《平议》的人留版面。<18>
可惜的是,《教务杂志》的倾斜政策,并没有因为这一批评,有多大的翻转变化。从1933年共12期的《教务杂志》看,赞同《平议》神学观点的文章,占了讨论《平议》之内容的大部份。反对《平议》神学观点的文章,大多以刊登保守派基督教机构对《平议》所作出的官方声明或关于官方声明之内容的摘要式报导为主,单独一位作者所撰写的反对文章尽管并非没有,也是少之又少。
(二)赞同《平议》的文章之分析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需要简单了解《平议》究竟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观点。《平议》的最后一章(以及《教务杂志》1933年第2期)归纳了全书重点,笔者在此仅将与本文史料分析密切相关的前四章之重点,简单陈明如下:
1、宣教机构必然应该继续存在,但是目的和方法却也绝对必须因应时代变化而变化。
2、差会的真正目的、也是自有差会以来唯一的目的:“愿你的国降临”。具体而言,即“与别国人民共同追求从耶稣基督言行里所表现出来的上帝的真智慧与慈爱;并且努力使他的精神在现代生活中发生影响。”
3、差会的工作范围:个人布道的“个人福音”依然很重要,但是“布道”一词同时也需要包括“用基督精神去供给人类的日常需要”的“社会福音”。同时,应该不让“差会所举办的教育及其他慈善工作”,“负担直接布道责任”;并鼓励宣教士,“甘愿将我们一切所有的,贡献与人,不必专在口头上,宣传福音”。
4、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宣教士的责任不在抨击其他宗教”,反而“应该认识并且了解”其他宗教,“然后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同点,相互携手”。并且,《平议》坚持,“基督教的真理能否为人类所接纳,并不在其他宗教的腐败或窳劣,而在其他宗教的健全与优良。”<19>
以上便是《平议》一书前四章的核心观点,乍看上去似乎中规中矩,并无激进之处。但是实际上,如此化约的陈述其观点,并不足以展示霍金等委员会成员在《平议》中的论证过程,以及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偏好。这些暂且留至后两节再讨论。在此,我们继续分析《教务杂志》中对于《平议》表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之态度的文章。
乐灵生不仅在第3期的编者言之中表达其观点,还就《平议》的内容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在第3期和第12期),并在另外3期的编者言(第4、8、11期)之中讨论之。毋庸讳言,出自持自由派神学立场的乐灵生之手的这些文章,均完全赞同《平议》对当下宣教事业的批判以及变革建议。例如,就《平议》的总体评论而言,乐灵生指出,《平议》的内容,对于许多人而言,充满了他们未曾预料的评论;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到今天,对《平议》的反应中,批评而非称赞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形给人一种印象:宣教士似乎不太热衷于改进自己的服务,而更热衷于为自己辩护。然而,他相信,《平议》中对宣教事业的批评不会因为被反对而成为无效。<20> 这篇充斥着“惊叹号”(字面含义的“惊叹号”)的评论文章,到处可见乐灵生几近狂热地——笔者认为这么说并非不恰当——对于《平议》表示拥护。乐灵生在文中呼喊着:“这个运动(即宣教事业的改革运动——引者注)还会继续!”“这个运动不可能被阻止!”(惊叹号为原文所有)<21>
又如,就“差会的工作范围”而言,乐灵生批评在现代基督教运动的发祥地,宗教很大程度上变成“个人化的”;它的目标是产生个人的洁净、平安、灵性的安全感和美好生活。但是,现代世界和现代人也需要宗教显示其“社会性的力量”。<22> 于是,在宣教工场,也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宣教服务:旧的类型是“用相对简单的方法,将福音外传”(只注重个体化的灵魂),而新的类型则是“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渗入社会环境之中”(显示宗教的社会性力量)。根据乐灵生的判断,在变革了的世界中,第二种类型的服务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3>
再如,就“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而言,乐灵生认为,不同宗教徒之间的合作,未必会以一个“混合式的宗教”而告终——尽管乐灵生也承认,《平议》中的一些语词,有朝这个方向倾斜的趋势。但是,乐灵生坚持,更多的用语清楚表明,《平议》的作者并无这种“混合主义”的想法。<24>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站在自由派神学立场的《教务杂志》编辑乐灵生本人,对于《平议》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不过,将《平议》定性为“自由派之作”,未必所有人都会认同。乐灵生自己就提出辩护,认为《平议》没有尝试要陈述“一个”神学体系。实际上,没有所谓“平议的神学”这一说,有的只是十五种神学(因为《平议》是由十五名评审委员共同署名的)的暂时性联合。<25> 评审委员会的主席霍金也承认,“有一件可庆的事,就是本委员会内部,对于基督教及宣教事业的看法,颇不一致。因为这样,才能代表北美各宗派的意见”。<26>
但是,在1932年11月的《平议》发布会上,霍金承认,《平议》的神学是“最终决定这个报告站得住脚或站不住脚的问题”;但他也清楚表示,评审委员会的十五位成员(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没有一个人对于《平议》中的同意是勉强的。<27> 一位宣教士亦提到,实际上《平议》的神学令“所有人”都不满意;因为这份报告是需要每一个委员都能够诚实地签上名,因此它只能表达委员们所一致同意的那些观点。<28> 另有一位宣教士恰恰是因为委员们妥协之后的观点,以“简单的术语呈现基督教的信息”,而对《平议》赞赏不已。<29> 还有一位宣教士,将《平议》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走出“宗派主义”,“超越宗派障碍和教义障碍”,向着“合一”作出的一次努力。一方面,《平议》尊重差异,当中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另一方面,《平议》致力于承认两派的共同信仰和“最小共识”,并建立一个包容的立场,在其中,自由派不会牺牲自由,保守派不会牺牲更完满的教义宝藏。<30>
只是,也的确有宣教士,在赞同《平议》神学观点的同时,坦然承认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很明显就是自由派神学立场。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美以美会宣教士指出,尽管《平议》作为“美国自由派更正教”的产物有其限制所在,但《平议》亦揭示了海外宣教中的真正议题,解放了基督徒的思想;这些没有官方地位阻碍的平信徒,不需要顾及那些关于“信经的理论”,鼓励宣教士集中关注耶稣伟大的个人生命的“魅力和诱人的能力”:它实际上挑战我们,重新考虑基督徒的目标,应该是“以基督的灵而活”,而不是“宣讲一个关于他的信息”。<31>
究竟,《平议》透露出来的神学立场是如何?它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达成的“最小共识”,还是自由派观点的昭然若揭?实际上,认同后一种观点的,不单只有前述那位赞同《平议》神学观点的宣教士而已,还有那些批评《平议》的宣教士和基督教机构。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那些反对《平议》的声音。
四、“别的福音”?
(一)反对《平议》的官方声明之分析
前文提到,很有可能是因为《教务杂志》及其主编乐灵生的自由派神学立场的缘故,1933年全年所刊登在《教务杂志》上反对《平议》神学观点的文章,多数是一些保守派基督教机构对《平议》所作出的官方声明或关于官方声明之内容的摘要式报导;仅若干文章是单独一位作者所撰写的——这与赞同《平议》神学观点的文章,完全不成比例。不过,至少值得肯定的是,自由派神学立场并没有使得《教务杂志》将所有批判《平议》神学立场的文章彻底抹杀,仅刊登有利于自由派神学立场的文章。透过这些保守派基督教机构对《平议》所作出的官方声明或关于官方声明之内容的摘要式报导,以及两篇与官方声明无关的文章,可以听到反对《平议》的声音如何发出。
我们首先分析保守派基督教机构对《平议》所作出的官方声明或关于官方声明之内容的摘要式报导。1933年4月,产生于1920年的一个属于基要派的宣教士机构、拥有超过1000名宣教士会员的中华圣经联会(The Bible Union of China)<32> 发表官方声明,指责《平议》带头发动了近代以来对宣教事业的“最大胆、最坚决的攻击”;它不仅提出宣教方法上的剧烈革命,而且是对福音信息本身的公开反对。简而言之,《平议》所宣扬的,其实是“别的福音”(another Gospel)。中华圣经联会认定,《平议》中占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对海外宣教的神学、宗教和心理基础的讨论,明显不是基于调查结果而写,<33> 而是来自委员会委员们先在的自由派观念,而一些坚持的、富有攻击性的自由派的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借此机会传播他们的神学立场。尤其是,该联会认为,就“差会的工作范围”而言,《平议》蔑视讲道,以之为愚蠢的(foolishness of preaching);就“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而言,《平议》视“基督作为唯一的拯救之路”的观点为“过时的”。该联会重申自己忠实于“圣经与福音派信仰”,依然认定讲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方法,它无论在哪一种类型的宣教服务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基督依然是人类唯一的拯救。<34>
同样强烈反对《平议》神学观点的,还有同属保守派阵营的基督教会同盟(the League of Christian Churches)和“信心差会”之一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包括一些重要的华人基要派领袖在内(如贾玉铭和杨绍唐)的基督教会同盟的官方声明,同中华圣经联会一样,严斥《平议》是“近几十年来,对福音派信仰最激烈的一次攻击”。在重申该同盟的“基要信仰”(包括上帝无谬误的圣言和福音中所揭示的基督作为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为代赎而死、身体复活,并且此福音与其他宗教信条相比是独一且终极的<35>)之后,再次反对《平议》藉着忽视基督的独一性、忽视主耶稣作为通向上帝的唯一之路的排他性地位,以及忽视福音的超自然的、救赎的力量,想要移走宣教事业的“历史基础和圣经基础”,并以“人本主义的理想主义”取代之。<36> 与基督教会同盟相似,内地会通过正式决议,重申其对原初“宣教目的、宣教信息以及新约使命的绝对忠心”,强烈反对《平议》,指责《平议》的目的显然是要用“纯然关于社会进步的人本信息”,替换“福音派关于神圣恩典与重生大能的福音”。<37>
我们发现,如上三个基要派背景的基督教机构,均对《平议》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指斥其背后的自由派神学,批评其背叛真福音,反而传扬现代的、理性化的“别的福音”。除了上述三个基督教机构,还有其他基督教机构或同样重申其“基要信仰”,并且批评《平议》偏离了这些信仰;<38> 或反对《平议》过于强调物质的服务,而轻视灵性的服务;<39> 或表示无法接受《平议》的“宗教混合主义”的意味。<40> 还有基督教机构指出,在《平议》三百多页的篇幅(指英文原版)之中,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被指为主,祷告和罪只被提到一次,而且很随意,圣灵和圣经则完全被忽略;并引用《圣经·使徒行传》4章12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重申基督信仰的独一性。<41>
总而言之,这些基督教机构的官方声明,总体而言反映了它们所认定《平议》具有的如下特性:忽视基督教的“基要信仰”;否定布道本身的重要性;过于强调宣教事业应转向社会参与和服务,建设地上天国;将基督教的独一真理相对化,主张更多与其他宗教对话,以至于有“宗教混合主义”的强烈倾向。
(二)反对《平议》的文章之分析
以上分析了一些保守派基督教机构对《平议》的反对意见。笔者接下来则简要归纳并分析《教务杂志》中两篇反对《平议》神学观点的文章。
在一篇题为《<平议>忽略了什麽》(What the Laymen Overlooked)的文章中,公理会宣教士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对《平议》感到“彻底的失望”。他批评《平议》讨论宣教事业之原则,与宣教事业的实情毫不相干;这些原则,不过是可以应用于评审委员会按自己的立场所赞同的那些宣教工作。与《平议》针锋相对,福开森以赞赏的口吻回忆早期的宣教士,就“宣教的目的”而言,他们并没有所谓“对于东方人的灵性的关注”(《平议》的倾向);他们有的是很强烈的对传讲“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2节)的渴望。他们没有要“探索全世界的道德合一”(同样是《平议》的倾向);他们所相信的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如前文的基督教机构所引用的《圣经·使徒行传》4章12节)。至于过去四十年来受国际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感召而来到宣教工场的宣教士,也与早期的宣教士受到的激励的来源一样:没有一个志愿者是为了回应“东方人的灵性幸福”而来的;是“基督的爱”催逼他们来的。
易言之,在福开森看来,所谓关注“东方人的灵性幸福”和“探索全世界的道德合一”,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宣教事业的目标,并非宣教事业本应该有的目标。宣教事业的正当目标,应是在“基督的爱”的催逼下,向尚未听闻福音的人传讲“基督并祂钉十字架”。<42>
就“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而言,福开森认为《平议》对于早期宣教士的指责是不公允的。恰恰是早期的宣教士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人,最先开始欣赏其他宗教的优点,并开始翻译它们的典籍;他们的翻译表明,他们总是很渴望指出这些宗教中所有好的东西。但是,《平议》中从没有把成就归给这些宣教士;相反,《平议》建议现代宣教有必要积极努力地去了解和明白它周围的宗教,此种建议好像显得这对于宣教士而言是一件新事。<43>
与福开森一样,大英长老会的宣教士道格拉斯·詹姆斯(T. W. Douglas James)也为宣教士先驱们辩护,认为他们已经在用实际行动(如宣教士自己研读儒家经典,又如神学生被要求了解“四书”,还如许多研究中国宗教的书之出版)更多了解他们身边的宗教。<44> 以上两位作者以这些事实,试图证明宣教士一直没有忽略了解宣教地的文化和宗教。
不过,詹姆斯称,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与其他伟大的信仰建立联系,而在于如何处理“迷信”;而这个问题恰恰被《平议》以一种轻而易举的方式忽略了。他依然“愚昧地”坚持,宣教地的信仰系统中,的确有“偶像崇拜”的成份——尽管这样的用语可能会被评审委员会嘲笑。<45>
最后,就“差会的工作范围”而言,詹姆斯犀利地指出,从总体上看,《平议》对“作为一种方法的‘讲道’十分抵触”;这是一种“讲道恐惧症”(a preaching phobia)。尽管《平议》中也并非完全戒绝用话语(in word)来布道,但是它非常倾向于在社会服务中用行动(in deed)来布道,而尽量少用话语来布道。没错,“讲道”确实有被滥用的情形;但是,詹姆斯认为,《平议》因此就废弃“讲道”而不用,这是不值得的。“讲道的力量”,作为一种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所说的“一种宗教经验的表达”,应该被保留。<46> 换言之,“讲道”在宣教事业中,至少仍应该与社会服务处于同等地位(如果不是更重要于社会服务的话)。
五、代结论——在文本与批判之间
以上,笔者分别析论了对于《平议》神学观点的不同态度。我们发现,对于同一个文本,居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赞同者以《平议》为宣教士的朋友,提出为因应世界文化之变革,宣教事业需要作出的改变,若伤害了宣教士,也是出于忠诚的缘故;反对者却以之为宣教事业乃至基督信仰的大敌,认为《平议》所宣扬的是一种敌对真福音的“别的福音”。笔者亦指出,原来就不同的或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神学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个宣教士或基督教机构对《平议》所持的看法。但是,且不论哪一方的神学立场才是“正确的”,从以上研讨中都自然生出一个疑问,即那些反对《平议》神学观点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平议》文本的实情?就本文关心的“神学立场”这一议题而言,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平议》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份我们如今所界定为自由派的报告?
我们在此只简要谈两个方面,也就是反对者对《平议》头四章的其中两个重点的批判,分别是“差会的工作范围”与“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关于这两方面的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平议》的神学取向。其一,是“差会的工作范围”。通常所认为的自由派在关于宣教中的“直接布道”和“社会服务”的关系上,一般都过于强调“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 emphasis in missions),却缺乏“直接布道”的热情(enthusiasm for direct evangelism)。<47> 这也确实是反对《平议》神学观点者对其极力批判的一个方面(例如,认为《平议》有“讲道恐惧症”),但这些反对者的批判有无道理?《平议》的作者以及为《平议》辩护的人称,《平议》并没有忽视“个人布道”;他们所要做的,是扩大“布道”(evangelism)一词的含义,将那些为不少宣教士所轻视的“社会服务”也视为“布道”之重要方面。因为,“福音宣传的本身,除非用社会事业来补充,并不完备”;更重要的是,“行道胜于讲道”。社会服务这一“间接布道”的好处在于,“不以传道为目的,而自然收获传道的果效”,而且它“并不完全废掉口舌的功用,因为如果有人要求时,仍须为之解释基督教生活的理由及方法”(着重号为引者加)。<48>
不过,《平议》在另外两处的行文,分别以提问和主张的表述,明显表示有必要改变以“社会服务”为“工具”的看法,似乎不单要纠正以往“社会服务”的劣势地位,更有以之取代“直接布道”的趋势:“如果我们可以藉着物质及社会的途径,达得灵性生活,那末,我们是否应继续地以传道为我们的中心事业,而以其他工作为辅佐?应否仍以一切慈善工作,为引人入教的工具?”因此,他们的建议是,“应使宣教事业中的教育及他种慈善工作,不负直接宣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应当表现克己的精神而不必用口宣讲”(着重号为引者加)。<49> 很明显,就此所讨论的“传福音与社会服务”的判准而言,《平议》的确是站在自由派神学的立场。
其二,是“差会对于其他宗教应有的态度”。通常所认为的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弱化基督教的独一性、绝对性和最终性,并倾向于“宗教调和主义”。 <50> 坚持认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宣教士,在这一点上,对《平议》尤其表示失望甚至愤怒。不过,《平议》的作者会辩称,他们只是主张“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必须尽力了解他种宗教,并须与旨趣相同者互相携手”;而且在基督教与非基督宗教互相交流,共同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基督教的特殊性”不会“有所损失”。<51>
但是,问题在于,《平议》作者所认为基督教的“特殊性”,主要指的是基督教的“中心教义”的“简单性”,亦即耶稣所表明的“两大诫命所说明的摩西律法”、“作为行为守则的黄金律”、“说明祈祷的主祷文”亦即“作为神学精义的天父的象征”。而这些所谓“适合现代人”的“简单”教义,只涉及“作为教师和模范”(as a teacher and model)的耶稣,却完全没有提到人类的罪和审判,以及“作为主和救主”(as Lord and Savior)的基督与十字架的救恩这些基要教义。<52> 相反,《平议》认为,海外宣教事业的原初动机——“没有听见福音的机会,其灵魂有受地狱永苦的危险……而生命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因着“神学思想的变迁”、“世界文化的发轫”和“东方民族主义的勃兴”这些变革,而不再“继续有效”。其中,尤其在“神学思想的变迁”方面,《平议》的作者相信,现代人“对于地狱的观念”已经改变,不再注重“上帝的惩罚及灭亡者所受的永刑”(现在注重的是“比较乐观的命运说”),而且关注的问题已经“从出世的兴趣到现世的罪恶及痛苦”。当下的基督教,在《平议》的作者看来,“无论它对于来世的生命,持何种态度,总不会再看诚信他种宗教的人,为不能得救;因此,它救人灵魂脱离永苦的动机,不及救人使不丢失至善的动机之更为坚固”。如今,“一个太注重超自然界如天堂地狱及其作用等等的宗教,不见得会惹起现代人的注意”。<53> 这样的神学立场,恰是保守派所极力抵抗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核心特质。<54>
因此,从上述文本和批判之间的对照看,保守派攻击《平议》,认为它是自由派的“党派”文本,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究竟孰是孰非,本文已不能再加以申述。只不过,这些西方宣教士之间就现代神学议题的辩护和反对,同样影响中国基督徒至深,因此由不得我们淡漠视之。或许,恰如那位与宣教士普天德讨论《平议》的中国基督徒教师所说,“得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信息是什么。”
<1> Gordon Poteat, “As a China Missionary Sees the Laymen’s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16.
<2>“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2 (December 1933), 761-762.该书在美国出版以后,美国的教会“无论为毁为誉,咸为瞩目”。参见诚静怡,“序”,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编、徐宝谦等译,《宣教事业平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3> Paul G. Hayes, “Our Book Table: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ppraisal of the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44;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ficial Statements on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59.
<4>“平信徒海外宣教事业调查”的发起人、资助者和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多数并不是“平信徒”这个中文词的一般语义令我们联想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参The Bible Union of China, “A Statement and a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Laymen’s Foreign Mission Inquiry and Appraisal,”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76; H. Van Etten, “The Urgency of Self-examin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9 (September 1933), 586。
<5>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等,“原序”,《宣教事业平议》,第1—3页。
<6>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2.
<7>洛克菲勒曾主张,教会若要存活,只有再寻回大量基督徒的忠诚,这些基督徒感觉教会的教义是令人窒息的,教会的道德立场是伪善的。教会因此必须变得更包容,不过多关注那些排他的、使人分裂且分散注意力的教义或形式。参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48-149。
<8>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150.针对《平议》本身,梅钦曾坦言:这份报告是“对历史的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参D. G. Hart, Defending the Faith: J. Gresham Machen and the Crisis of Conservative Protestantism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8。
<9> Jan Van Lin, Shaking the Fundamentals: Religious Plurality and Ecumenical Movement (Amsterdam: Rodopi, 2002), 131-132.
<10>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158-175.
<11>“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2 (February 1933), 67; Wynn C. Fairfield, “A Close-Up of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69; John C. Ferguson, “What the Laymen Overlooked,”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500; “Presbyterian (North) Board on Laymen’s Inquiry,”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540.
<12>“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2 (February 1933), 67.
<13>“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2 (February 1933), 68-69.评审委员会的主席霍金也曾说:“这份报告(指《平议》——引者注),是从一些基督徒给予另一些基督徒的报告……我们联合在基督的爱之中,热切、非常热切地渴望祂的精神可以散播至这个失常的、破碎的、受苦的、罪恶的世界。”参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ficial Statements on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58。又如,诚静怡在《平议》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平信徒调查团的发言人“都是我教的忠实信徒,中坚分子,与无的放矢,意存破坏者,不可同日而语。”参前引诚静怡,“序”。
<14>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67.
<15> Ibid., Chapter 2.
<16>“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38.
<17> Ibid.
<18> J. E. Shoemaker,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5 (May 1933), 322-323.
<19>《宣教事业平议》,第73—76页。
<20>在第4期的编者言中,乐灵生指出,批评是属灵成长的刺激因素,如果我们以正确的心对待之的话。参“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06。乐灵生还在第8期的编者言中说:“批评是宣教士每一餐的调味汁!基督教的恩典应该使得宣教士能将批评转化为藉着重新调整和自我改进而进步的标准。”参“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488。
<21> The Editor, “Thinking Forward with the Laymen: Review Article,”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58-160.
<22> “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06-207.
<23>“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489.在另外一处,乐灵生批评宣教士,指出大体而言,宣教士相当个人主义化,且没有为他们的现代任务而充足预备好。参The Editor, “The Facts About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12 (December 1933), 807。
<24> The Editor, “Thinking Forward with the Laymen: Review Article,”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63.
<25>甚至,乐灵生力图使《平议》与自由派撇清界限,认为《平议》的态度不是“一个犹豫的、虚弱的、宽容的、无力的‘自由派的’基督教,在这种基督教的灵魂中,坚定的信仰已经消失了”。参”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1 (November 1933), 700。
<26>霍金等,“原序”,前引《宣教事业平议》,第4—5页。在此,霍金所指的“不一致”的意见包括:1、认为宣教事业是“吾人对于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完美的启示,人神圆满交通唯一的道路——效忠最高的表示”;2、认为宣教事业是“一种利他精神的表现,为与全人类同享基督教文化之果的一种愿望”;3、认为宣教士是“为人类共同追求上帝的一种努力,借以充分实现在个人及团体生活里天赋的可能性”。
<27> F. R., “The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nd Sponsors of the Laymen’s Foreign Inquiry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47.
<28> Frank T. Cartwright, “Appraising the Laymen’s Appraisal of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72.
<29> W. P. Mills, “Theological Basis of the Laymen’s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21.
<30> Paul G. Hayes, “Cooperation in Christian Mis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Proposed in the Laymen’s Inquiry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11, 415-416, 418.
<31> Paul G. Hayes, “Our Book Table: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ppraisal of the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44-245.
<32>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
<33>该联会认为,委员会中几乎没有人对保守的教会团体和宣教机构有兴趣,因此,《平议》中的结论不可以认为是不偏不倚的评估。参The Bible Union of China, “A Statement and a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Laymen’s Foreign Mission Inquiry and Appraisal,”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76-477。
<34>同上,第476—478页。“中华圣经联会”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他们所反对的自由派所传扬的福音,是“另一种福音”;那些传讲的人,是“传讲另一种福音者”。参前引《为真道争辩》,第71、81、83页。这种类型的批评,似乎是基要派对自由派常见的批评,如中国的基要主义者陈崇桂,就认定那些“传耶稣的主义人格”之人所传扬的是“别的福音”。参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香港:宣道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35>华人基要派领袖王明道,在其著作中也提到类似的基要信仰。参王明道,《我们是为了信仰!》,香港:灵食季刊社,1955年,第1—3页。其他的教会历史学家也同样强调基要派的五点核心要义,参前引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第22页。
<36>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Christian Churches,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Layman’s Foreign Missionary Inquiry,”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80.
<37> Faith Missions, “Official Statements on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57.
<38>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ficial Statements on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60.
<39>中国医学协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的“医学宣教委员会”(Council on Medical Missions)从医疗宣教的角度出发,认为《平议》无法意识到现代医疗是要强调身体、心灵和灵魂的相互关系,《平议》的观点却是要回到只是纯粹关乎身体的医疗方法。将那呈现于耶稣基督中的上帝之爱的全备福音,传给宣教医院的每一个病人,是宣教士医生工作的一个部份;这并非强加给病人,而是引导他们过一种包含了身体健康和灵性健康之应许的生活方式。该委员会最后强调,医疗宣教的核心主旨,是属灵的主旨,即个人与基督的关系;这应该且必须成为所有真正的宣教努力的背后动机。但是,《平议》却根本没有承认这一点作为参与宣教工作的资格,该委员会感到极为失望。参Council on Medical Missions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Official Statements on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57。
<40>“Methodists and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10 (October 1933), 687.
<41>“‘Rethinking Missions’: Action Taken by the Chosen Mission of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in March 1933,” The Chinese Recorder 11 (November 1933), 753.
<42> John C. Ferguson, “What the Laymen Overlooked,”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500-501, 504.
<43> Ibid., 501.
<44> T. W. Douglas James, “‘Re-Thinking Missions’ and China’s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515.
<45> Ibid., 515-516.
<46> Ibid., 518-519.
<47>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103.
<48>宣教事业平议》,第55—56、284页。亦参“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2 (February 1933), 73-74; Wynn C. Fairfield, “A Close-Up of ‘Re-Thinking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3 (March 1933), 168; Gordon Poteat, “As a China Missionary Sees the Laymen’s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4 (April 1933), 210-211; Paul G. Hayes, “Cooperation in Christian Mis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Proposed in the Laymen’s Inquiry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13; W. P. Mills, “Theological Basis of the Laymen’s Report,” The Chinese Recorder 7 (July 1933), 422-423; Roderick Scott, “New Missions or New Bottles? What is New About the Laymen’s Report? ,”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497; F. Ufford, “Evangelism through Shar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8 (August 1933), 511, 513。
<49>《宣教事业平议》,第57、59页。
<50>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Chapter 6.
<51>《宣教事业平议》,第30页。
<52>一位日本基督徒曾这样评论《平议》:“《平议》试图向我们阐释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并将此视为基督教……为了上帝的国来临,付出十字架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平议》丝毫没有提及。”参Jonathan J. Bonk, Missions and Money: Affluence as a Missionary Problem Revisite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6), 186。
<53>《宣教事业平议》,第10、18、43页。
<54>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104.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名誉副研究员,目前正在攻读加拿大艾尔伯塔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华人基督教史、加拿大基督教史和数字人文。)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1期的主题是“时代变局中的基督徒知识人·民国初年”,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